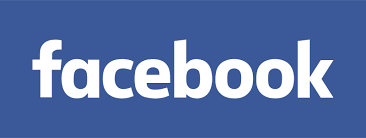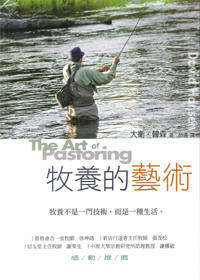гҖҖгҖҖдёҖжң¬зү§йӨҠеӯёзҡ„經典д№ӢдҪң
гҖҖгҖҖгҖҢжҲ‘жғіиҰҒжүҫзү§её«пјҺпјҺпјҺгҖҚ
гҖҢзү§её«еҺ»йҮЈйӯҡдәҶе•ҰпјҒгҖҚ
йҖҷжҳҜдёҖжң¬иҲҮзңҫдёҚеҗҢзҡ„зү§йӨҠжӣёпјҢеӣ зӮәдҪңиҖ…еӨ§иЎӣвҖ§йҹ“жЈ®е°ұжҳҜдёҖеҖӢиҲҮзңҫдёҚеҗҢзҡ„зү§её«гҖӮ
йҹ“жЈ®зҡ„ж•ҷеҚҖдҪҚж–јең°е»ЈдәәзЁҖзҡ„зҫҺеңӢи’ҷеӨ§жӢҝе·һпјҢжүҖд»Ҙд»–йңҖиҰҒеңЁе…©еҖӢйғЎд№Ӣй–“еҫҖиҝ”пјҢеҗҢжҷӮзү§йӨҠе…©й–“дёҚеҗҢе®—жҙҫзҡ„ж•ҷжңғпјҢжҮүд»ҳе…©еҘ—жңғиҰҸгҖҒе…©зЁ®й•·еҹ·еҲ¶еәҰгҖҒе…©жү№жңғеҸӢиҲҮеҗҢе·ҘпјҺпјҺпјҺд»ҖйәјдәӢжғ…йғҪиҰҒеҒҡе…©д»ҪгҖӮд»–еҫһдёҚеңЁж•ҷжңғиЈЎжҺЁиЎҢдҪҲйҒ“иЁҲз•«гҖҒз®ЎзҗҶж–№жЎҲгҖҒжҺўиЁӘиЁ“з·ҙпјҢдҪҶжҳҜжңғеҸӢжҷӮжҷӮеҲ»еҲ»йғҪеңЁеӮізҰҸйҹіпјҢе…©й–“ж•ҷжңғиүұеӣ°зҡ„иІЎеӢҷйғҪжӯҘдёҠдәҶжӯЈи»ҢпјҢиҖҢдё”д»–жҜҸеӣһеҺ»йҶ«йҷўжҺўиЁӘжҷӮпјҢдёҖе®ҡдёҚжҳҜж•ҷжңғ裡第дёҖеҖӢе ұеҲ°зҡ„дәәгҖӮиҖҢд»–пјҢз«ҹ然йӮ„жңүеҘҪеӨҡжҷӮй–“еңЁйўЁе…үжҳҺеӘҡзҡ„еұұжһ—й–“дҝЎжӯҘжј«йҒҠпјҢеңЁжҳ и‘—и—ҚеӨ©зҷҪйӣІзҡ„жё…жҫҲжәӘжөҒиЈЎйҮЈйұ’йӯҡпјҒ
йҖҷеҖӢзү§её«жҳҜжҖҺйәјз•¶зҡ„пјҹ
йҹ“жЈ®еҜ«еҮәйҖҷжң¬гҖҠзү§йӨҠзҡ„и—қиЎ“гҖӢеҫҢпјҢжңүз„Ўж•ёзү§её«еҫһдёӯеҫ—и‘—е°ӢиҰ“е·Ід№…з”ҡиҮіеӨұе–Әе·Ід№…зҡ„ж„ҹеӢ•иҲҮжҝҖеӢөпјҢйӣ–然дёҚе°‘дәәеүӣй–Ӣе§Ӣи®Җзҡ„жҷӮеҖҷйғҪй©ҡи©«дёҚе·ІпјҡеҺҹдҫҶпјҢзү§йӨҠжҳҜйҖҷжЁЈзҡ„пјҒ
жҳҜзҡ„пјҢйҹ“жЈ®иҰҒиӘӘзҡ„е°ұжҳҜпјҡзү§иҖ…иҰҒеңЁеҗ„зЁ®жғ…жіҒдёӢжҲҗзӮәиҖ¶з©Ңзҡ„жҜ”е–»пјҢйҖҷжүҚжҳҜзү§йӨҠзҡ„жң¬иіӘгҖӮиҖ¶з©Ңз”ЁжҜ”е–»и®“дәәй ҳжңғжң¬дҫҶдёҚжҳҺзҷҪзҡ„еӨ©еңӢд№ӢйҒ“пјӣзү§иҖ…зҡ„жүҖиЁҖжүҖиЎҢжүҖжҳҜпјҢд№ҹиғҪи®“еҺҹдҫҶдёҚжҳҺзҷҪзҘһжҒ©е…ёзҡ„дё–дәәй ҳжңғзҘһжҒ©е…ёзҡ„еҗҢеңЁпјҢйҖІиҖҢиҮӘе·ұд№ҹжҙ»еҮәеҹәзқЈзҡ„жЁЈејҸпјҢжҲҗзӮәиҖ¶з©Ңзҡ„жҜ”е–»гҖӮйҖҷе°ұжҳҜзү§иҖ…зҡ„дәӢеҘүгҖӮ
йҖҷжң¬жӣёдёҚжңғж•ҷдҪ жҖҺжЁЈиӨҮиЈҪжҲҗеҠҹзҡ„зү§йӨҠжҠҖе·§пјҢиҖҢжҳҜйӮҖи«ӢдҪ иёҸдёҠеұ¬ж–јиҮӘе·ұзҡ„жҺўзҙўд№Ӣж—…пјҢжҠҠдҪ зҡ„дәӢеҘүпјҢиӯңеҜ«жҲҗдёҖеҖӢеҸҲдёҖеҖӢеӮійҒ”еҹәзқЈжң¬иіӘзҡ„жҜ”е–»пјҢз”ЁдҪ зҡ„з”ҹе‘ҪпјҢжҙ»еҮәзү§йӨҠзҡ„и—қиЎ“гҖӮ
еҗҚдәәжҺЁи–Ұ
ж–°еә—иЎҢйҒ“жңғдё»д»»зү§её«ејөиҢӮжқҫ
д»Ҡж—ҘеңЁж•ҷжңғдёӯжҳҜеҗҰд№ҹжңүзӘ®еҝҷж—ҸпјҹжҠҠжҷӮй–“зІҫзҘһеӨ§йҮҸжҠ•е…ҘдёҖеҖӢиҪҹйҡҶйҡҶйҹҝзҡ„йҒӢиҪүж©ҹеҷЁв”Җв”ҖиҒҡжңғ敬жӢңжҙ»еӢ•пјҢеҚ»жІ’жңүд»»дҪ•зҡ„з”ўеҮәпјҒйҖҷжҳҜдҪ зҡ„еҳҶжҒҜе—ҺпјҹйҖҷжң¬гҖҠзү§йӨҠзҡ„и—қиЎ“гҖӢдҪҝжҲ‘еҖ‘зңӢиҰӢжӣҷе…үпјҒ
в”Җв”ҖиІҙж јжңғеҗҲдёҖе Ӯзү§её«гҖҖеҫҗеқӨйқ–
дҪңиҖ…жүҖеҲҶдә«зҡ„жҳҜд»–иҰӘиә«зү§жңғзҡ„й ҳеҸ—пјҢиЁұеӨҡе…§е®№жҳҜзү§жңғеҜҰйҡӣйқўиҮЁзҡ„е•ҸйЎҢпјҢ當жҲ‘еңЁзү§жңғдёӯиҰӘиә«з¶“жӯ·е’Ңй«”й©—жҷӮпјҢе°ұжӣҙиғҪиҲҮдҪңиҖ…з”ўз”ҹе…ұйіҙпјҢд№ҹйҖІдёҖжӯҘжҸҗйҶ’е’ҢжҝҖеӢөжҲ‘зҡ„дәӢеҘүгҖӮ
в”Җв”ҖдҝЎеҸӢе Ӯдё»д»»зү§её«гҖҖи¬қжҰ®з”ҹ
зӣёдҝЎжң¬жӣёдҪңиҖ…зҡ„й«”жңғпјҢе°ҚиЁұеӨҡеңЁд»»еӢҷе°Һеҗ‘зҡ„зү§жңғдёӯпјҢж„ҹиҰәиҮӘе·ұжүҖдҪңжүҖзӮәжјёжјёеӨұеҺ»еұ¬йқҲж„Ҹзҫ©иҲҮзӣ®жЁҷзҡ„еӮійҒ“дәәпјҢжңүи§ЈжҜ’иҲҮжҝҖеӢөд№Ӣж•ҲгҖӮ
в”Җв”ҖдёӯеҺҹеӨ§еӯёе®—ж•ҷз ”з©¶жүҖе°Ҳд»»еҠ©зҗҶж•ҷжҺҲ еҳүзҫ©еҹәзқЈж•ҷйҶ«йҷўиҮЁеәҠеҝғзҗҶеё«гҖҖи¬қеЁңж•Ҹ
еңЁдҪ еҸҜиғҪи®ҖеҲ°зҡ„ж•ҷзү§жӣёзұҚд№ӢдёӯпјҢйҖҷжҳҜжңҖд»ӨдәәиҖізӣ®дёҖж–°пјҢд№ҹжңҖеқҰзҺҮиӘ еҜҰзҡ„дёҖжң¬гҖӮ
в”Җв”Җз•ўеҫ·з”ҹпјҲEugene H. Petersonпјү
гҖҖгҖҖеӨ§еӯёжҷӮи’ҷеҸ¬е…ЁиҒ·дәӢеҘүпјҢзҘһеӯёйҷўз•ўжҘӯеҫҢдҫҝдёҖзӣҙеңЁзҫҺеңӢи’ҷеӨ§жӢҝе·һй„үй–“зү§йӨҠе°ҸеһӢж•ҷжңғпјҢе°Үиҝ‘дәҢеҚҒијүд№ӢеҫҢпјҢй ҶеҫһзҘһзҡ„её¶й ҳпјҢйҒ·иҮідҝ„дәҘдҝ„е·һзҡ„иҫӣиҫӣйӮЈжҸҗзү§йӨҠеӨ§еһӢж•ҷжңғпјҢеҰӮд»Ҡд»ҚеңЁиҫӣиҫӣйӮЈжҸҗдәӢеҘүгҖӮйҹ“жЈ®зү§её«еёёеңЁгҖҠй ҳиў–жңҹеҲҠгҖӢпјҲLeadership JournalпјүзҷјиЎЁж–Үз« гҖӮгҖҠзү§йӨҠзҡ„и—қиЎ“гҖӢжҳҜд»–зҡ„第дёҖжң¬и‘—дҪңгҖӮ
гҖҖгҖҖеҸҰеӨ–и‘—жңүпјҡ
гҖҖгҖҖ•гҖҠйқҲйӯӮе°ӢиҰ“жҢҮеҚ—гҖӢпјҲжҡ«иӯҜпјү
гҖҖгҖҖA Little Handbook on Having a Soul (InterVarsity Press, 1997)
гҖҖгҖҖ•гҖҠиҲҮдё»еҗҢйҒҠпјҡжҠҠжёёжҖқеҢ–зӮәзҘҲзҰұгҖӢпјҲйҷійҢҰжҰ®иӯҜпјҢйҰҷжёҜпјҡеӯёз”ҹзҰҸйҹіеңҳеҘ‘пјҢ2006пјү
гҖҖгҖҖLong Wandering Prayer (InterVarsity Press, 2001)
гҖҖгҖҖ•гҖҠж„ӣдҪ й ҳе°Һзҡ„ж•ҷжңғгҖӢпјҲжҡ«иӯҜпјү
гҖҖгҖҖLoving the Church You Lead (Baker Books, 2004)
жҺЁи–ҰеәҸдәҢпјҡжҸ®еҲҘеұ¬йқҲзӘ®еҝҷж—ҸвҲ•еҫҗеқӨйқ–пјҺпјҺпјҺ8
жҺЁи–ҰеәҸдёүпјҡи®“дҪ зҡ„дёҖз”ҹжҲҗзӮәиҖ¶з©Ңзҡ„жҜ”е–»вҲ•и¬қеЁңж•ҸпјҺпјҺпјҺ11
иҮҙи¬қпјҺпјҺпјҺ13
д»ЈеәҸпјҺпјҺпјҺ15
иҮӘеәҸпјҺпјҺпјҺ17
еј•иЁҖпјҡд»Ҙдҫҝд»Ҙи¬қзҡ„ж•…дәӢпјҺпјҺпјҺ20
第дёҖз« гҖҖй–Ӣз«ҜпјҺпјҺпјҺ27
第дәҢз« гҖҖе‘јеҸ¬пјҺпјҺпјҺ47
第дёүз« гҖҖиҒ–йқҲпјҺпјҺпјҺ65
第еӣӣз« гҖҖи©ҰжҺўпјҺпјҺпјҺ89
第дә”з« гҖҖзөӮжң«пјҺпјҺпјҺ111
第е…ӯз« гҖҖеӮійҒ“пјҺпјҺпјҺ131
第дёғз« гҖҖзҘҲзҰұпјҺпјҺпјҺ149
з¬¬е…«з« гҖҖеҸӢиӘјпјҺпјҺпјҺ167
第д№қз« гҖҖиҒ–зҰ®пјҺпјҺпјҺ189
第еҚҒз« гҖҖй ҳе°ҺпјҺпјҺпјҺ205
第еҚҒдёҖз« гҖҖйӣўдё–пјҺпјҺпјҺ229
第еҚҒдәҢз« гҖҖзҚҺиіһпјҺпјҺпјҺ241
еҫҢиЁҳпјҺпјҺпјҺ250
йҷ„йҢ„дёҖпјҡиҷ•иҷ•йўЁжҷҜпјҺпјҺпјҺ256
йҷ„йҢ„дәҢпјҡиЎЁйқўд№ӢдёӢпјҺпјҺпјҺ267
йҷ„иЁ»пјҺпјҺпјҺ274
е•ҸйЎҢиЁҺи«–пјҺпјҺпјҺ279
第дёҖз« гҖҖй–Ӣз«Ҝ
жҲ‘з”ЁйӣҷжүӢжҚӮдҪҸиҮүеҸ–жҡ–пјҢдҪҶж“ұеңЁжЎҢйқўдёҠзҡ„жүӢиӮҳд»Қ然ж„ҹеҲ°еҲәйӘЁзҡ„еҜ’еҶ·гҖӮйӣ»з·ҡйӮ„жҳҜиҲҠејҸеҢ…еёғйӣ»з·ҡзҡ„иҖҒйӣ»жҡ–еҷЁпјҢи®“е®Өе…§з©әж°Јжјёжјёжҡ–е’Ңиө·дҫҶгҖӮ
зңӢдёҚиҰӢжҲ‘е‘јеҮәзҡ„зҷҪж°ЈдәҶгҖӮдёҚйҒҺйҗөиЈҪзҡ„жӣёжЎҢжҡ–еҫ—йқһеёёж…ўпјҢз°ЎзӣҙжҠҳзЈЁдәәгҖӮжҲ‘еҮҚеЈһдәҶпјҢеҶ·еҲ°жІ’иҫҰжі•и®ҖжӣёгҖӮ
жҲ‘зҡ„иҫҰе…¬е®ӨдҪҚж–ји’ҷеӨ§жӢҝй„үй–“дёҖжүҖзӨҫеҚҖж•ҷжңғпјҢеҠ и“ӢеңЁжңғе Ӯе»әзҜүзҡ„йӮҠдёҠгҖӮиҫҰе…¬е®Өж—ўжІ’жңүеЈҒејҸжҡ–зҲҗпјҢд№ҹжІ’жңүдёӯеӨ®з©әиӘҝпјҢжӣҙжІ’жңүйҡ”зҶұиЈқзҪ®гҖӮ
жҜҸеӨ©ж—©жҷЁйҖҷеҖӢең°ж–№йғҪеҫ—йҮҚж–°з”Ёйӣ»жҡ–еҷЁеҠ зҶұпјҢжүҚиғҪеҶҚеәҰжҡ–е’Ңиө·дҫҶгҖӮж–°е№ҙ已經йҒҺеҺ»е…ӯеҖӢжҳҹжңҹдәҶпјҢйҖҷиЎЁзӨәиҮӘжҲ‘з”ҹ平第дёҖ次擔當зү§иҒ·иҮід»ҠпјҢ已經жңүе…ӯеҖӢжҳҹжңҹдәҶгҖӮеӨ–й ӯжҳҜйӣ¶еәҰзҡ„еҶ°й»һпјҢжӯЈйңҸйңҸйЈ„и‘—йӣЁйӣӘгҖӮ
жӯӨеҲ»пјҢжҲ‘зҡ„йқҲйӯӮиЈЎд№ҹжӯЈйӣЁйӣӘзҙӣйЈӣпјҢйҷҚеҲ°еҶ°й»һпјҢдёҚзҹҘйҒ“и©ІжҖҺйәјиҫҰгҖӮжҲ‘и’ҷзҘһе‘јеҸ¬пјҢжҺҘеҸ—ж•ҷиӮІиЁ“з·ҙпјҢ經йҒҺеҜҰзҝ’пјҢз№јиҖҢиў«д»»е‘ҪжҲҗзӮәзү§иҖ…гҖӮ
жҲ‘зҹҘйҒ“иҮӘе·ұжңүдёҖеӨ§е ҶеҲҶе…§е·ҘдҪңиҰҒеҒҡпјҢеҚ»дёҚзҹҘ究з«ҹи©ІдҪңеҖӢд»ҖйәјжЁЈзҡ„зү§её«гҖӮжҲ‘еҝғиЈЎж—ўеҶ°еҶ·еҸҲжҒҗжҮјгҖӮе…¶еҜҰжҲ‘жңүеҘҪеӨҡеҘҪеӨҡдәӢиҰҒеҒҡпјҢиҰҒжҳҜиә«й«”еҲҘеҶҚеҶ·еҫ—жҠ–еҖӢдёҚеҒңе°ұеҘҪдәҶгҖӮ
еҶ¬еҺ»жҳҘдҫҶпјҢиҮӯйј¬жңғе°ӢжүҫдёҖеҖӢйҡұеҜҶзҡ„е·ўз©ҙпјҢдәӨй…Қз№Ғж®–еҫҢд»ЈгҖӮжҲ‘еҖ‘йҖҷеә§жңғе Ӯзҡ„еҹәзҹіе·Із¶“зўҺиЈӮпјҢе°ҚиҮӯйј¬дҫҶиӘӘжңүеҰӮдёҖиҒІиҒІжә«жҡ–зҡ„е‘је–ҡгҖӮйӮЈдәӣиЈӮзё«жң¬иә«е°ұеӢқйҒҺеҚғиЁҖиҗ¬иӘһпјҢеҘҪеғҸеңЁе°ҚиҮӯйј¬иӘӘпјҡгҖҢжӯЎиҝҺдҪ еҖ‘еҲ°ж•ҷжңғдҫҶпјҒгҖҚ
жҲ‘еҖ‘жҠҠж•ҷжңғзңӢжҲҗжҳҜдёҖеҖӢ家пјҢеҠӘеҠӣж»ҝи¶іжңғеҸӢзҡ„йңҖжұӮгҖӮ然иҖҢеҸ—ж•ҷжңғз…§йЎ§жңҖеӨҡзҡ„пјҢжҒҗжҖ•е°ұжҳҜиҮӯйј¬дёҖ家еӯҗгҖӮ
ең°жқҝдёӢйқўзҡ„ж°ҙйӣ»з®Ўи·Ҝз©әй–“д№ҫзҮҘиҖҢйҷ°жҡ—пјҢж”ҫзҪ®еңЁжҲ¶еӨ–зҡ„еһғеңҫжЎ¶еҸҲиҖҒжҳҜиў«жөҒжөӘзӢ—зҝ»еҖ’еңЁең°гҖӮеҒҘеә·зҡ„и’ҷеӨ§жӢҝиҮӯйј¬пјҢиҒһиө·дҫҶз°ЎзӣҙеғҸзҮ’з„Ұзҡ„ијӘиғҺгҖӮжҳҘеӨ©иЈЎйЈ„йҖІжҲ‘иҫҰе…¬е®Өзҡ„еҲәйј»ж°Је‘іпјҢдёҚзҰҒи®“жҲ‘е°ҚеҜ’еҶ¬дёӯеҗёе…Ҙзҡ„еҶ°еҶ·з©әж°Јеҝғеӯҳж„ҹжҝҖгҖӮ
жҲ‘жӯЈеңЁзө„еҗҲеёҢиҮҳж–ҮеӢ•и©һзҡ„еӯ—е°ҫи®ҠеҢ–пјҢең°жқҝдёӢеӮідҫҶиҮӯйј¬е•ғеӣ“зҡ„йҹҝиҒІпјӣжҲ‘з”ЁеҠӣдёҖи·әи…іпјҢиҒІйҹіе°ұжІ’дәҶгҖӮдҪҶжҲ‘дёҖеӣһеҲ°еёҢиҮҳж–ҮдёҠйқўпјҢйӮЈжғұдәәзҡ„иҒІйҹіеҸҲдҫҶдәҶгҖӮ
жҲ‘зҹҘйҒ“ж•ҷжңғе°ҚжҲ‘зҡ„жңҹеҫ…жҳҜд»ҖйәјпјҡиҰҒеңЁзү§йӨҠй—ңжҮ·иҲҮй ҳе°Һжңғзңҫе…©ж–№йқўйғҪеӢқд»»ж„үеҝ«пјҢиҰҒжҢүжҷӮеҮәзҸҫеңЁиҫҰе…¬е®ӨпјҢйӮ„иҰҒи¬ӣйҒ“зІҫйҮҮгҖӮ
жҲ‘жң¬дҫҶд№ҹеёҢжңӣиҮӘе·ұеҸҜд»ҘиҝҺеҗҲйҖҷдәӣеҗҲзҗҶзҡ„жңҹеҫ…гҖӮдҪҶжҳҜжҲ‘зҸҫеңЁзҹҘйҒ“пјҢжҲ‘дёҚиғҪи®“ж•ҷжңғдҫҶе‘ҠиЁҙжҲ‘жҲ‘жҳҜиӘ°гҖҒжҲ‘зҡ„е·ҘдҪңи©ІжҖҺйәјеҒҡгҖӮ
з•ўз«ҹд»–еҖ‘йҖЈжҲ‘зҡ„иҫҰе…¬е®ӨйңҖиҰҒжҡ–ж°ЈйҖҷжЁЈз°Ўе–®зҡ„дәӢжғ…йғҪзңӢдёҚеҮәдҫҶгҖӮжҲ‘й–Ӣе§ӢиіӘз–‘зңјеүҚзҡ„еӣ°еўғгҖӮ
еҲ°еә•иҫҰе…¬е®Өжңүжҡ–ж°ЈжҳҜдёҚжҳҜжҲ‘жҮүеҫ—зҡ„е‘ўпјҹ
жҳҜпјҢжҲ‘еҖјеҫ—гҖӮ
жңғеҸӢйӣЈйҒ“йғҪжҳҜеҗқе—Үзҡ„е°Ҹж°Јй¬је—Һпјҹ
дёҚжҳҜпјҢд»–еҖ‘д»ҳзөҰжҲ‘еҫҲеҘҪзҡ„и–ӘиіҮгҖӮжҲ‘д№ҹе–ңжӯЎйҖҷдәӣдәәгҖӮ
д»–еҖ‘爲д»ҖйәјдёҚжӣҝжҲ‘зҡ„иҫҰе…¬е®Өжғій»һиҫҰжі•пјҹ
жҲ‘дёҚзҹҘйҒ“гҖӮ
д»–еҖ‘е°ҚжҲ‘зҡ„е·ҘдҪңжңүжІ’жңүйӮЈйәјдёҖдёҒй»һе…’зҡ„иӘҚиӯҳе•Ҡпјҹ
жІ’жңүпјҢд»–еҖ‘дёҰдёҚдәҶи§ЈгҖӮ
жҲ‘жғіи®“йҖҷдәӣдәәдҫҶе‘ҠиЁҙжҲ‘жҲ‘жҳҜиӘ°гҖҒи©ІеҒҡдәӣд»Җйәје—ҺпјҹеҲҘеҝҳдәҶпјҢе°ұжҳҜд»–еҖ‘зөҰжҲ‘йҖҷжЁЈдёҖй–“иҫҰе…¬е®ӨпјҢи®“жҲ‘еҲ°дәҶеҶ¬еӨ©е°ұе·®й»һеӨұжә«еҮҚжӯ»пјҢдёҖеҲ°жҳҘеӨ©еҸҲйҡӘдәӣзӘ’жҒҜиҖҢдәЎгҖӮ
жҲ‘дёҚжғігҖӮ
е№ҫе№ҙд»ҘеҫҢпјҢйӣ»жҡ–еҷЁеЈһдәҶпјҲжҲ‘зҢңеӨ§жҰӮжҳҜиў«иё№дәҶеӨӘеӨҡи…ізҡ„з·Јж•…пјүпјҢж–јжҳҜжҲ‘зөӮж–јеҫ—еҲ°дёҖеҘ—еЈҒејҸжҡ–ж°ЈиЁӯеӮҷгҖӮдҪҶжҳҜз”ұж–јең°жқҝдёҖзӣҙжІ’еһ®пјҢжүҖд»ҘжІ’ж©ҹжңғж•ҙдҝ®ең°еҹәпјҢиҮӯ鼬家ж—Ҹд№ҹе°ұйҖҷжЁЈдёҖзӣҙеҫ…дәҶдёӢеҺ»гҖӮ
жҲ‘д№ӢжүҖд»ҘеҝҚеҸ—йҖҷдәӣзӢҖжіҒпјҢжҳҜеӣ зӮәйҖҷдәӣдәӢжғ…дҪҝжҲ‘жҳҺзҷҪпјҢжҲ‘еңЁж•ҷжңғдәӢеҘүзҡ„жҷӮеҖҷпјҢдёҰдёҚжҳҜеңЁ爲ж•ҷжңғе·ҘдҪңгҖӮжҲ‘еҫһдҫҶдёҚжғіжҲҗзӮәж•ҷжңғзҡ„йӣҮе·ҘпјҢиҖҢжҲ‘д№ҹеҫһжңӘи®ҠжҲҗдёҖеҖӢйӣҮе·ҘгҖӮжҲ‘жҳҜд»–еҖ‘зҡ„зү§иҖ…гҖӮ
жҲ‘зҡ„йӣҮдё»жҳҜиҖ¶з©ҢеҹәзқЈгҖӮжңҚдәӢж•ҷжңғжҳҜеҮәж–јжҲ‘е°ҚеҹәзқЈзҡ„й ҶжңҚгҖӮиҖ¶з©ҢжҳҜжҲ‘зҡ„иҖҒй—ҶпјҢжҳҜзҘӮеҗ©е’җжҲ‘жҜҸеӨ©з•¶еҒҡд»ҖйәјгҖӮ
дёҖйқўжә–еӮҷи¬ӣз« дёҖйқўеҶ·еҫ—зҷјжҠ–пјҢиҝ«дҪҝжҲ‘иӘҚжё…иҮӘе·ұ究з«ҹжҳҜеңЁ爲иӘ°й җеӮҷи¬ӣз« пјҡжҲ‘жҳҜзӮәиҖ¶з©ҢеҹәзқЈеҒҡзҡ„пјҢиҖҢиҖ¶з©ҢжғіжҠҠжүӢиӮҳж“ұеңЁжЎҢдёҠйғҪжІ’еҫ—ж“ұв”Җв”ҖзҘӮеҫһдҫҶжІ’жңүеҸҜе®үжӯҮзҡ„ең°ж–№гҖӮж•ҷжңғеӣ жӯӨиҒҪеҲ°жҲ‘жӣҙзІҫйҮҮзҡ„и¬ӣйҒ“гҖӮ
зҘһеӯёе®¶е°ҚгҖҢж•ҷзү§дәӢеҘүгҖҚзҡ„е…ёеһӢеҸҚжҮүпјҢе°ұжҳҜжҠҠе®ғжӯёеҲ°гҖҢж•ҷжңғгҖҚйҖҷеҖӢеӨ§йЎҢзӣ®д№ӢдёӢгҖӮжҲ‘當然жӣүеҫ—з®ҮдёӯйҮҚй»һпјҡж•ҷжңғеҸ¬е–ҡзү§иҖ…еҺ»еҒҡж•ҷжңғиЈЎжңҖйҮҚиҰҒзҡ„е·ҘдҪңпјҢиҖҢзү§иҖ…еүҮжҠҠзҘһиЁ—д»ҳзөҰж•ҷжңғзҡ„ж–ҪжҒ©жүӢж®өиЎҢдҪҝеҮәдҫҶпјҢзӣҙеҲ°дё»еҶҚдҫҶзҡ„жҷӮеҖҷгҖӮйҖҷиғҪиӘӘжҳҺжҲ‘зҡ„е·ҘдҪңпјҢеҚ»з„Ўжі•иӘӘжҳҺжҲ‘зҡ„жң¬иіӘгҖӮ
жҲ‘жңҚдәӢж•ҷжңғпјҢд№ҹжЁӮж–јдәӢеҘүгҖӮжҲ‘жҳҺзҷҪпјҢ當жҲ‘й–Ӣе§Ӣзү§йӨҠдәӢеҘүпјҢе°ұиЎЁзӨәжҲ‘иҰҒеҝ еҝғжңҚдәӢж•ҷжңғпјҢиҮіжӯ»ж–№дј‘гҖӮжҲ‘еҸӘеёҢжңӣиҮӘе·ұжҳҜзӮәдәҶжӯЈзўәзҡ„еҺҹеӣ иҖҢиғҢиө·еҚҒеӯ—жһ¶гҖӮжҲ‘дёҚжғіеӣ зӮәзҳӢзӢӮең°爲ж•ҷжңғиҷ•зҗҶж•ёдёҚжё…зҡ„йӣңеӢҷиҖҢйҒҺеӢһжӯ»гҖӮ
дәӢеҜҰдёҠпјҢйҒҺд»Ҫзҡ„иҰҒжұӮйғҪдёҚжҳҜдҫҶиҮӘж–јжңғеҸӢгҖӮд»–еҖ‘еӨ§еӨҡеёҢжңӣжҲ‘жҠҠе·ҘдҪңз°ЎеҢ–гҖӮеҫһд»–еҖ‘иҰҒжұӮжҲ‘еҺ»еҒҡзҡ„дәӢдёӯпјҢжҲ‘еҸҜд»ҘеҲҶиҫЁгҖҒжүҫеҮәжҲ‘и©ІеҒҡзҡ„дәӢгҖӮ
йҖҷжүҚжҳҜеҗҲд№ҺиҒ–經зҡ„еҹәзӨҺй ҳе°ҺеӯёгҖӮжҳҜжҲ‘иҮӘе·ұжҠҠжңҹжңӣе Ҷеҫ—еӨӘй«ҳпјҢжҠҠдәӢжғ…еј„иӨҮйӣңдәҶгҖӮжҲ‘йңҖиҰҒжӣҙйҒ©еҲҮзҡ„жЁҷжә–дҫҶжұәе®ҡжҲ‘зҡ„е·ҘдҪңж„Ҹзҫ©гҖӮ
йҖҷи¶ҹйҮЈйӯҡд№ӢиЎҢдёҚеӨ§й ҶеҲ©гҖӮжҲ‘иө°дәҶе…©иӢұйҮҢзҡ„и·ҜпјҢеҸӘйҮЈеҲ°е…©жўқйӯҡгҖӮзҸҫеңЁжҲ‘дҫҶеҲ°дәҶйҗөеҲәз¶ІеңҚзұ¬йӮҠдёҠпјҢйҖҡеёёжҲ‘йғҪжҳҜиө°еҲ°йҖҷиЈЎе°ұеӣһй ӯиёҸдёҠжӯёйҖ”гҖӮеҰӮжһңжҲ‘еҢҚеҢҗи‘—еҫһйҗөеҲәз¶Іеә•дёӢзҲ¬йҒҺеҺ»пјҢеҸҜиғҪжңғжҜҖдәҶйҖҷйӣҷйҳІж°ҙй•·зӯ’йқҙпјҢд№ҹеҸҜиғҪйҒҮдёҠз”ҹж°Јзҡ„ең°дё»иҝҪи‘—жҲ‘и·‘гҖӮ
然иҖҢпјҢжҺўзҙўж–°ж°ҙеҹҹзҡ„жҷӮеҖҷеҲ°дәҶгҖӮжүҖд»ҘпјҢжҲ‘зҡ„й•·зӯ’йқҙйӮ„жҳҜжүҜз ҙдәҶпјҢйҮЈйӯҡи®Ҡеҫ—жҜ”ијғй ҶеҲ©пјҢз”ҹж°Јзҡ„ең°дё»д№ҹжІ’жңүеҮәзҸҫгҖӮжҲ‘и·ЁйҒҺеҖ’еңЁең°дёҠзҡ„жЈүзҷҪжҘҠжЁ№е№№пјҢеҘ®еҠӣеңЁй•·иҚүй–“иёҸеҮәдёҖжўқи·ҜдҫҶпјҢдёҖйқўе°ҸеҝғдёҚиҰҒи·Ңи·ӨпјҢдёҖйқўз•ҷж„ҸжІійқўпјҢе°ӢжүҫйҒ©еҗҲеһӮйҮЈзҡ„ең°ж–№гҖӮ
жҲ‘жІҝи‘—жІіеІёиө°пјҢжІіеІёжңүеҘҪе№ҫе‘Һй«ҳпјҢеІёеқЎйҷЎеіӯпјҢзӣҙиҗҪж·ұдёҚеҸҜжё¬зҡ„жІіеә•гҖӮдёҚйҒҺжҲ‘зҡ„зңјзқӣе°ҲжіЁзӣҜи‘—еүҚж–№зҡ„и·Ҝеҫ‘гҖӮдёҖеҖӢеҝөй ӯй–ғйҒҺпјҢжҲ‘зӘҒ然жҳҺзҷҪдәҶиҮӘе·ұжҳҜиӘ°гҖҒеҒҡзҡ„жҳҜд»ҖйәјдәӢгҖҒзӮәд»ҖйәјйҖҷжЁЈеҒҡиЎҢеҫ—йҖҡгҖӮд»ҘеүҚжҲ‘жӣҫ經еӯёйҒҺпјҡиҖ¶з©ҢжҳҜдёҠеёқзҡ„жҜ”е–»гҖӮ
жҲ‘дёҚиғҪеҸ–д»ЈиҖ¶з©ҢпјҢжҲ‘дёҚжҳҜдёҠеёқзҡ„жҜ”е–»гҖӮеҸҜжҳҜ當жҲ‘и·ҹйҡЁиҖ¶з©ҢеҹәзқЈпјҢжҲ‘е°ұеҸҜд»ҘжҲҗзӮәиҖ¶з©Ңзҡ„жҜ”е–»пјҢйӮЈе°ұжҳҜжҲ‘пјҢе„ҳз®Ўе°ҡжңӘе®Ңе…ЁпјҢдҪҶжҲ‘е°ұжҳҜиҖ¶з©Ңзҡ„жҜ”е–»гҖӮйҖҷе°ұжҳҜзү§иҖ…зҡ„жң¬иіӘв”Җв”Җзү§иҖ…жҳҜиҖ¶з©Ңзҡ„жҜ”е–»гҖӮ
жҠҠи·ҹйҡЁиҖ¶з©Ңзҡ„иЎҢеӢ•и·ҹзү§йӨҠдәӢеҘүзҡ„иЎҢеӢ•иҒҜжғіеңЁдёҖиө·пјҢи©ІеҫһдҪ•иӘӘиө·е‘ўпјҹжҲ‘йңҖиҰҒжҠҠйҖҷ兩件дәӢй—ңиҒҜиө·дҫҶпјҡгҖҢжҲ‘жҳҜиӘ°пјҹиә«зӮәи·ҹйҡЁеҹәзқЈзҡ„дәәпјҢжҲ‘жҮү當жҖҺйәјжҙ»пјҹгҖҚ
д»ҘеҸҠгҖҢжҲ‘жҳҜиӘ°пјҹиә«зӮәзү§её«пјҢжҲ‘иҰҒеҒҡд»ҖйәјпјҹгҖҚжҲ‘йҖҷж®ҳз ҙдёҚе…Ёзҡ„з”ҹе‘ҪпјҢиҰҒжҖҺйәјеҸҚжҳ еҮәйӮЈдҪҚиҰӘиҝ‘дәәзҡ„ж°ёжҙ»е®Үе®ҷдё»е®°пјҹиҰҒжҖҺжЁЈжҠҠйҖҷдҪҚдё»её¶йҖІжҲ‘йӮЈзҫӨжңғеҸӢзҡ„ж—Ҙеёёз”ҹжҙ»пјҹд»–еҖ‘зҡ„з”ҹе‘Ҫд№ҹеҗҢжЁЈж®ҳз ҙдёҚе…ЁгҖӮ
дёҠеёқзҡ„йҒ“е‘ҠиЁҙжҲ‘еҖ‘пјҡгҖҢд»–йҶ«еҘҪеӮ·еҝғзҡ„дәәпјҢиЈ№еҘҪд»–еҖ‘зҡ„еӮ·иҷ•гҖӮ
д»–ж•ёй»һжҳҹе®ҝзҡ„ж•ёзӣ®пјҢдёҖдёҖзЁұд»–зҡ„еҗҚгҖӮгҖҚпјҲи©©дёҖеӣӣдёғ3пҪһ4пјүжҲ‘дёҖи·ҜдёҠи·Ңи·Ңж’һж’һпјҢж‘ёзҙўи‘—еҰӮдҪ•йҶ«жІ»еӮ·еҝғзҡ„дәәгҖҒеӯёзҝ’зәҸиЈ№д»–еҖ‘зҡ„еӮ·иҷ•пјҢиҖҢйӮЈдҪҚжҺҢз®Ўжҳҹиҫ°гҖҒзҫӨеұұгҖҒжҙӢжө·зҡ„дёҠеёқд№ҹиЎҢдәҶеҘҮдәӢпјҢжҲҗе…ЁдәҶжҲ‘зҡ„дәӢеҘүпјҢйҖҷжҳҜжҲ‘еҫҢдҫҶеӯёеҲ°зҡ„гҖӮ
然иҖҢпјҢжҲ‘д№ҹеӯёеҲ°дәҶпјҢиӢҘеҸӘеҫһйҖ зү©дё»зҡ„и§’еәҰдҫҶиҰӢиӯүдёҠеёқпјҢд№ҹжңүеҸҜиғҪйҖ жҲҗйқһеёёеӨ§зҡ„иӘӨи§ЈгҖӮзҷҪйӣӘзҡҡзҡҡзҡ„еұұе·”еӣә然еЈҜи§ҖзҫҺйә—пјҢд№ҹжңғжҠ•е°„еҮәй»‘жҡ—зҡ„йҷ°еҪұгҖӮ
йӣўжҲ‘家дёүзҷҫзўјзҡ„ең°ж–№пјҢжңүдёҖеә§еіӯеЈҒеҫһйҰ¬йҪ’иҺ§жІіи°·жӢ”ең°иҖҢиө·пјҢй«ҳе…©зҷҫиӢұе°әпјҢи·қйӣўйҰ¬йҪ’иҺ§еұұи„Ҳдә”иӢұйҮҢгҖӮ
е…’еӯҗд№қжӯІеӨ§зҡ„жҷӮеҖҷпјҢжңүдёҖж¬ЎжҲ‘её¶и‘—д»–еҺ»зҲ¬йӮЈеә§еіӯеЈҒпјҢе…’еӯҗе•ҸжҲ‘пјҡгҖҢзҲёпјҢиҗ¬дёҖдёҠеёқдёҚеӯҳеңЁжҖҺйәјиҫҰпјҹгҖҚ趕еҝ«жғіеҖӢеҘҪеӣһзӯ”е•ҠпјҒдҪҶжҳҜпјҢжҲ‘еҸӘиғҪе‘ҠиЁҙд»–пјҡгҖҢжҲ‘зӣёдҝЎжңүдёҠеёқпјҢжҲ‘еёҢжңӣдҪ д№ҹдҝЎгҖӮ
дёҚйҒҺдҪ йҖҷдёҖз”ҹпјҢйӮ„жҳҜеҝ…й ҲиҮӘе·ұеҒҡеҖӢжұәе®ҡгҖӮгҖҚжҲ‘зҹҘйҒ“пјҢд»ҘеҸ—йҖ иҗ¬зү©дҪңзӮәиЁҙжұӮдҫҶиӯүжҳҺдёҠеёқеӯҳеңЁпјҢж—ҘеҫҢеҸҚиҖҢеҸҜиғҪе°ҺиҮҙд»–дёҚдҝЎгҖӮз•ўз«ҹпјҢдёҚдҝЎзҡ„дәәеӢ•дёҚеӢ•е°ұиӘӘд»–еҖ‘еҙҮжӢңзҡ„дәӢеӨ§иҮӘ然дёӯзҡ„дёҠеёқпјҢи—үжӯӨжҠҠжҲ‘жү“зҷјжҺүгҖӮ
дёҖжҠ№зҫҺйә—зҡ„еӨ•йҷҪдёҰдёҚиғҪе®ҡжҲ‘еҖ‘зҡ„зҪӘпјҢд№ҹдёҚиғҪдҪҝзҪӘеҫ—иөҰе…ҚгҖӮеҖҳиӢҘжҲ‘еңЁйҮҺеӨ–й«ҳең°ж·Ӣеҫ—жёҫиә«жҝ•йҖҸпјҢе°ұеҝ«еӨұжә«иҖҢжӯ»пјҢж—ҒйӮҠжЁ№дёҠзҡ„зғҸйҙүеҸӘжңғзңӢи‘—жҲ‘гҖҒжңҹзӣјжҲ‘еҝ«еҝ«еӨұжә«жӯ»жҺүпјҢзү е°ұжңүжқұиҘҝеҗғдәҶгҖӮжүҖд»ҘжӯӨжҷӮжӯӨең°пјҢжҲ‘еҝ…й ҲжҲҗзӮәеҹәзқЈзҡ„жҜ”е–»гҖӮ
гҖҢзү§её«гҖҚзҡ„ж„Ҹзҫ©еӣ жӯӨеӨ§зӮәдёҚеҗҢгҖӮзңҫдәә既然зҹҘйҒ“жҲ‘жҳҜ當ең°ж•ҷжңғзҡ„зү§её«пјҢиҮӘ然жңғжҠҠжҲ‘зҡ„дёҖиЁҖдёҖиЎҢи·ҹеҹәзқЈиҒҜжғіеңЁдёҖиө·гҖӮжҲ‘еҖ‘дёҖ家жҗ¬дҫҶдҪӣзҫ…еҖ«ж–ҜйҺ®еӨ§зҙ„еҚҠе№ҙеҫҢпјҢжҲ‘зҲ¶жҜҚеҫһиҸҜзӣӣй “е·һзҡ„ж–ҜеқЎеқҺпјҲSpokane, WashingtonпјүдёҖи·Ҝй–Ӣи»ҠдҫҶдҪӣзҫ…еҖ«ж–ҜжҺўжңӣжҲ‘еҖ‘гҖӮ
家зҲ¶иө°йҖІйҺ®дёҠдёҖй–“йӨҗйӨЁпјҢе•ҸжңүжІ’жңүдәәзҹҘйҒ“жҲ‘家дҪҸе“Әе…’гҖӮжңүеҖӢдәәиӘӘпјҡгҖҢе–”пјҢж–°дҫҶзҡ„зү§её«еҳӣгҖӮд»–дҪҸеңЁжі°иҲ’е··зҡ„йӮЈй–“жңЁеұӢпјҢеұұеқЎдёҠеҺ»дёҖй»һе°ұеҲ°дәҶгҖӮгҖҚд»–еҖ‘зҹҘйҒ“жҲ‘жҳҜиӘ°гҖӮе°Қд»–еҖ‘дҫҶиӘӘпјҢжҲ‘е°ұд»ЈиЎЁеҹәзқЈгҖӮ
еҫ·еңӢзҘһеӯёе®¶йӣІж јзҲҫпјҲEberhard Jüngelпјүзҡ„и‘—дҪңгҖҠзҘһжҳҜдё–з•Ңзҡ„еҘ§зҘ•гҖӢпјҲGod as the Mystery of the WorldпјүжҸҗеҮәдёҖеҖӢжҙһиҰӢпјҡиҖ¶з©ҢжҳҜдёҠеёқзҡ„жҜ”е–»гҖӮйӣІж јзҲҫи§ЈйҮӢйҒ“пјҡгҖҢжӯӨдёҖеҹәзқЈи«–йҷіиҝ°пјҢй ҲиҰ–зӮәдёҠеёқд№ӢеҸҜиЁҖиӘӘжҖ§зҡ„и©®йҮӢеӯёдёӯзҡ„еҹәжң¬е‘ҪйЎҢгҖӮгҖҚ
дёҠеёқзҡ„еҸҜиЁҖиӘӘжҖ§пјҲspeakabilityпјүпјҢжӯЈжҳҜжҲ‘е°ҚиҮӘе·ұз”ҹе‘Ҫзҡ„жңҹиЁұв”Җв”ҖжҲҗзӮәдёҖеҖӢжҙ»з”ҹз”ҹгҖҒжңғжҲҗй•·зҡ„з”ҹе‘ҪпјҢи®“дёҠеёқи—үи‘—жҲ‘иӘӘи©ұгҖӮжҲ‘дёҚжҳҜиӢұйӣ„пјҢеҸӘжҳҜдёҖеҖӢе№іеҮЎдәәпјҢеңЁж—Ҙеҫ©дёҖж—Ҙзҡ„е№іеҮЎз”ҹжҙ»дёӯеҠӘеҠӣж•Ҳжі•еҹәзқЈгҖӮ
е°ұз®—жңүжҷӮеҖҷжҗһз ёдәҶпјҢд№ҹеҸӘжңғдҪҝжҲ‘жӣҙеғҸиҒ–經дёӯйӮЈдәӣиӢұйӣ„дәәзү©гҖӮиӢҘжғіеңЁиҒ–經дёӯжүҫеҲ°е“ӘдёҖдҪҚдёҠеёқзҡ„еғ•дәәжҳҜеҫһжңӘзҠҜйҒҺеӨ§йҢҜзҡ„пјҢеҸҜеҫ—иҠұдёҠеҘҪдёҖз•Әе·ҘеӨ«гҖӮжӯЈеҰӮжҳ”жҷӮдёҖдҪҚиӢұеңӢжё…ж•ҷеҫ’жүҖиЁҖпјҡгҖҢдёҠеёқеҸӘжҸҖйҒёдәҶдёҖдҪҚе®Ңе…Ёзҡ„дәӢеҘүиҖ…гҖӮгҖҚ
жҜ”е–»жҳҜд»Җйәје‘ўпјҹжҜ”е–»е°ұжҳҜйҡұе–»пјҲmetaphorпјүзҡ„延伸гҖӮйӣІж јзҲҫиӘӘпјҡгҖҢжҜ”е–»еҸҜиҰ–зӮәйҡұе–»зҡ„延伸пјҢжҸӣиЁҖд№ӢпјҢйҡұе–»жҳҜз°ЎеҢ–еҫҢзҡ„жҜ”е–»гҖӮе…©иҖ…зҡ„е·®з•°е…¶еҜҰеңЁж–јжҜ”е–»жҳҜж•ҳдәӢпјҢйҡұе–»еүҮе°Үж•ҳдәӢжҝғзё®еңЁжҹҗеҖӢи©һиӘһд№ӢдёӯгҖӮгҖҚ
жҜ”е–»жҳҜдёҖеҖӢж•…дәӢпјҢеҲ»ж„ҸеңЁе·ІзҹҘдәӢзү©иҲҮжңӘзҹҘдәӢзү©д№Ӣй–“иЈҪйҖ дёҖзЁ®е°Қз…§й—ңдҝӮпјҢзӣ®зҡ„жҳҜзӮәдәҶиӘӘжҳҺйӮЈе°ҡжңӘзҹҘжӣүзҡ„дәӢзү©пјҢеҘҪеё¶зөҰиҒҪзңҫж„ҸжғідёҚеҲ°зҡ„嶄新жҖқз¶ӯгҖӮ
иҖ¶з©Ңзҡ„ж•…дәӢе°ұжҳҜдёҠеёқзҡ„жҜ”е–»пјҢеӣ зӮәиҖ¶з©ҢжҳҜеҸҜиҰӢзҡ„дәәеӯҗпјҢиҖҢдёҠеёқеүҮжҳҜдёҚеҸҜиҰӢзҡ„йқҲгҖӮиҖ¶з©Ңзҡ„з”ҹе№іе°ұжҳҜдёҠеёқзө•дҪізҡ„жҜ”е–»гҖӮ
иҖ¶з©Ңзҡ„дёҖз”ҹиҲҮзү§иҖ…зҡ„дёҖз”ҹжңүиЁұеӨҡзӣёдјјд№Ӣиҷ•гҖӮиҖ¶з©ҢеҸ—дёҠеёқе‘јеҸ¬пјҢй–Ӣе§ӢзҘӮзҡ„еӮійҒ“з”ҹж¶ҜгҖӮзҘӮеҸ—дәҶиҒ–йқҲзҡ„иҶҸжҠ№пјҢ經жӯ·йҒҺйӯ”й¬јзҡ„и©ҰжҺўгҖӮзҘӮе‘ҠиӘЎзңҫдәәпјҡд»Ҡз”ҹзҡ„зөҗжһңжңғ延зәҢеҲ°ж°ёз”ҹгҖӮзҘӮи¬ӣйҒ“гҖҒзҰұе‘ҠгҖҒйҶ«жІ»гҖҒиҲҮзҪӘдәәзӮәеҸӢгҖӮ
зҘӮеҸ—йӣЈжҳҜ爲дәҶдё–дәәпјҢд№ҹжҳҜ爲дәҶж•ҷжңғгҖӮзү§иҖ…д№ҹеҝ…й Ҳ經жӯ·йҖҷдёҖеҲҮгҖӮж №ж“ҡдёҠиҝ°жЁҷжә–пјҢжҲ‘зҡ„зү§йӨҠе·ҘдҪңе°ұжҳҜйҖҷдҪҚеҘҪзү§дәәжүҖ延伸еҮәдҫҶзҡ„йҡұе–»пјҢдҪңеҒҮдёҚеҫ—гҖӮд№ҹжғҹжңүеҰӮжӯӨпјҢжҲ‘зҡ„з”ҹе‘ҪжүҚиғҪеӮійҒһдёҠеёқжҒ©е…ёеҮәдәәж„ҸеӨ–зҡ„еҗҢеңЁгҖӮ
еӣ жӯӨпјҢ當жҲ‘иёҸе…ҘйҶ«йҷўз—…жҲҝжҺўиЁӘпјҢеӨ§е®¶еҘҪеғҸзңҹзҡ„й«”й©—еҲ°дёҠеёқдҫҶиЁӘгҖӮйҖҷжЁЈиӘӘдјјд№ҺеҫҲиҮӘиІ пјҢдёҚйҒҺжңүжҷӮеҖҷжҲ‘еҸӘжҳҜеҺ»е°ҸйӨҗйӨЁиЈЎи·ҹиӘ°иҰӢдёҖиҰӢи«ҮдёҖи«ҮпјҢеҚ»ж„ҹиҰәиҮӘе·ұеҘҪеғҸж №жң¬дёҚеңЁе ҙпјҢжҳҜдёҠеёқиҰӘиҮӘиҮЁеңЁгҖӮжңүжҷӮеҖҷпјҢдёҠеёқжҳҜеңЁжҲ‘и¬ӣйҒ“жҲ–зҰұе‘Ҡзҡ„當дёӯиҮЁеҲ°гҖӮ
е°ұйҖЈжҲ‘еңЁйӣңиІЁеә—иЈЎи·ҹдәәдёҚжңҹиҖҢйҒҮгҖҒе•ҸеҖҷдёҖдёӢиҝ‘жіҒпјҢдёҠеёқд№ҹиҲҮжҲ‘еҖ‘еҗҢеңЁгҖӮиә«зӮәиҖ¶з©Ңзҡ„жҜ”е–»пјҢжҲ‘зңӢеҮәдҫҶиҖ¶з©Ңе°Қй–Җеҫ’иӘӘзҡ„йҖҷеҸҘи©ұзңҹжңүеҸҜиғҪзҷјз”ҹпјҡгҖҢдәәжҺҘеҫ…дҪ еҖ‘е°ұжҳҜжҺҘеҫ…жҲ‘пјӣжҺҘеҫ…жҲ‘е°ұжҳҜжҺҘеҫ…йӮЈе·®жҲ‘дҫҶзҡ„гҖӮгҖҚпјҲеӨӘеҚҒ40пјүйҖҷдёҚжҳҜд»ҖйәјеӨӘиӨҮйӣңзҡ„йҒ“зҗҶпјҢжҺҘдёӢдҫҶзҡ„經ж–ҮдёӯпјҢиҖ¶з©Ңз№јзәҢиӘӘйҒ“пјҡгҖҢз„Ўи«–дҪ•дәәпјҢеӣ зӮәй–Җеҫ’зҡ„еҗҚпјҢеҸӘжҠҠдёҖжқҜж¶јж°ҙзөҰйҖҷе°ҸеӯҗиЈЎзҡ„дёҖеҖӢе–қпјҢжҲ‘еҜҰеңЁе‘ҠиЁҙдҪ еҖ‘пјҢйҖҷдәәдёҚиғҪдёҚеҫ—иіһиіңгҖӮгҖҚпјҲеӨӘеҚҒ42пјү
жҺҘеҫ…жҲ‘пјҢжҖҺйәје°ұжҺҘеҫ…дәҶеҹәзқЈе‘ўпјҹдёҖж–№йқўпјҢеңЁж–°зҙ„иҒ–經дёӯпјҢж•Ҳжі•еҹәзқЈжҳҜжүҖжңүжңҚдәӢзҡ„еҹәзӨҺпјҢйҖҷд№ҹжҳҜжҲ‘зҡ„е·ҘдҪңж ёеҝғгҖӮ
еҸҰдёҖж–№йқўпјҢжҲ‘йӣ–然ж•Ҳжі•еҹәзқЈпјҢжңүжҷӮеҚ»иЎЁзҸҫеҫ—зӣёз•¶жӢҷеҠЈгҖӮж„ҲжҳҜйҖҷзЁ®жҷӮеҖҷпјҢе°ұж„ҲйңҖиҰҒжҳҺзҷҪгҖҢжҜ”е–»гҖҚиҲҮгҖҢйҡұе–»гҖҚжңүдёҖй—ңйҚөзү№иүІпјҡжҜҸеҖӢжҜ”е–»гҖҒжҜҸеҖӢйҡұе–»пјҢжң¬иіӘдёҠе°ұжңүе…¶жҘөйҷҗпјҢдёҖж—ҰзҷјжҸ®еҲ°йҖҷжҘөйҷҗпјҢйЎһжҜ”зҡ„еҠҹиғҪе°ұдёӯжӯўдәҶгҖӮ
иҖҢдё”пјҢжғ…еўғдёҚеҗҢпјҢз”Ёжі•д№ҹдёҚеҗҢгҖӮеңЁзҙ„зҝ°зҰҸйҹідёӯпјҢиҖ¶з©Ңе‘ҠиЁҙжҲ‘еҖ‘иӘӘпјҡгҖҢжҲ‘жҳҜдё–дёҠзҡ„е…үгҖҚпјӣеңЁзҷ»еұұеҜ¶иЁ“дёӯпјҢд»–еҸҲе‘ҠиЁҙжҲ‘еҖ‘иӘӘпјҡгҖҢдҪ еҖ‘жҳҜдё–дёҠзҡ„е…үгҖҚгҖӮ
е„ҳз®ЎйҖҷе…©еҖӢйҡұе–»жүҖж¶өи“Ӣзҡ„зҜ„еңҚиҲҮжҘөйҷҗеҸҜи¬ӮеҚ—иҪ…еҢ—иҪҚпјҢдҪҶжҲ‘еҖ‘зҡ„зўәжҳҜдё–дёҠзҡ„е…үпјҢжҲ‘еҖ‘д№ҹзҡ„зўәеҝ…й ҲйЎҜжҳҺдёҰеӮіжҸҡйӮЈгҖҢзңҹе…үпјҢз…§дә®дёҖеҲҮз”ҹеңЁдё–дёҠзҡ„дәәгҖҚпјҲзҙ„дёҖ9пјүгҖӮ
дёҖзӣҙеҲ°жҲ‘еҫҢдҫҶзөӮж–јжұәе®ҡй–Ӣе§ӢдҫҶж•ҷжңғпјҢд№ҹиӘҚиӯҳдәҶдҪ пјҢжҲ‘жүҚжҳҺзҷҪжҲ‘д»ҘеүҚдёҚжҳҜзңҹзҡ„еңЁиәІдҪ пјҢжҲ‘е…¶еҜҰжҳҜеңЁиәІдёҠеёқгҖӮгҖҚж–јжҳҜпјҢжҲ‘еҸҲжҮӮдәҶиҖ¶з©ҢиӘӘйҒҺзҡ„еҸҰдёҖеҸҘи©ұжҳҜд»Җйәјж„ҸжҖқпјҡгҖҢжЈ„зө•дҪ еҖ‘зҡ„е°ұжҳҜжЈ„зө•жҲ‘пјӣжЈ„зө•жҲ‘зҡ„е°ұжҳҜжЈ„зө•йӮЈе·®жҲ‘дҫҶзҡ„гҖҚпјҲи·ҜеҚҒ16пјү
✽✽✽
жҲ‘жҳҜд»ҘиҮӘе·ұзҡ„иә«еҲҶеҺ»еҲ°жңғзңҫзҡ„家дёӯпјҢд»–еҖ‘ж·ұзҹҘжҲ‘жҳҜиӘ°гҖӮеӣ зӮәжҲ‘д№ҹжҳҜд»Ҙзү§иҖ…зҡ„з«Ӣе ҙйҖ иЁӘпјҢжүҖд»ҘжҲ‘жҺўиЁӘзҡ„家еәӯжү“еҫһдёҖй–Ӣе§Ӣе°ұзҹҘйҒ“пјҢжҹҗдәӣеұ¬ж–јдёҠеёқзҡ„дәӢжғ…жӯЈеңЁйҖІиЎҢгҖӮ
жҲ‘еӮҫиҒҪд»–еҖ‘иЁҙиӘӘд»–еҖ‘зҡ„ж•…дәӢпјҢзӣЎеҠӣдёҚеҺ»жғіиҮӘе·ұйӮЈдәӣдёҚиЁҺдёҠеёқе–ңжӮ…гҖҒиҮӘжҲ‘дёӯеҝғзҡ„иЁҲз•«пјҲгҖҢдҪ еҖ‘зӮәд»ҖйәјдёҚеёёдёҠж•ҷжңғдҫҶе‘ўпјҹжҲ‘жғіиҰҒж•ҷжңғеўһй•·пјҢдҪ еҖ‘еҸҜжҳҜжҲ‘йҖҷиЁҲз•«зҡ„дёҖйғЁеҲҶе“ӘгҖӮгҖҚпјүгҖӮ然еҫҢпјҢжҲ‘зӮәйҖҷдёҖ家дәәзҰұе‘ҠгҖӮ
дҪ еҸҜиғҪжғіеғҸдёҚеҲ°пјҢиҒҶиҒҪд»–дәәжҳҜеӨҡйәјйҮҚиҰҒзҡ„дёҖ件дәӢгҖӮ然иҖҢдёҠеёқжүҖеҒҡзҡ„пјҢе°ұжҳҜиҒҶиҒҪжҲ‘еҖ‘зҡ„еҝғиҒІгҖӮ
дәӢеҜҰдёҠпјҢеҰӮжһңжҲ‘иғҪз”ЁиҖ¶з©ҢиҒҶиҒҪжҲ‘еҖ‘зҡ„ж–№ејҸдҫҶиҒҶиҒҪйҖҷдёҖ家дәәзҡ„еҝғиҒІпјҢе°ұжңғеңЁд»–еҖ‘е…§еҝғж·ұиҷ•еҪўжҲҗдёҖеҖӢе°Қз…§гҖӮд»–еҖ‘зҡ„жҪӣж„Ҹиӯҳжңғе‘ҠиЁҙд»–еҖ‘пјҡиҖ¶з©ҢиҒҪеҲ°дәҶжҲ‘зҡ„еҝғиҒІпјӣиҖ¶з©Ңе°ұжҳҜйҖҷжЁЈеӯҗгҖӮд»–еҖ‘жңғж„ҸиӯҳеҲ°пјҢиҮӘе·ұе…¶еҜҰдёҖзӣҙеңЁе’ҢиҖ¶з©Ңи«ҮеҝғгҖӮ
жҲ‘жҳҜдёҚжҳҜйҒҺж–јжёҙжңӣиӯүжҳҺиҮӘе·ұзҡ„иә«еҲҶпјҢз”ҡиҮіж–јжҠҠиҮӘе·ұ當дҪңиҖ¶з©ҢдәҶе‘ўпјҹдёҚжҳҜзҡ„пјҢжҲ‘еҸӘдёҚйҒҺжҳҜдёҖж №з¶Ғи‘—зҫҪжҜӣе’ҢзөІз·ҡзҡ„йҮЈйүӨзҪ·дәҶгҖӮ
жҲ‘зҷјзҸҫпјҢжҲ‘иҲҮдәәеҖ‘зӣёйҒҮжҷӮпјҢд»–еҖ‘иҲҮдёҠеёқзӣёдәӨзҡ„й«”й©—пјҢеӨҡйҒҺж–јд»–еҖ‘иҲҮжҲ‘еҖӢдәәдәӨеҫҖзҡ„й«”й©—гҖӮйҖҷжЁЈзҡ„зӢҖжіҒиҰҒжҖҺйәји§ЈйҮӢе‘ўпјҹв”Җв”Җеӣ зӮәжҲ‘е°ұжҳҜиҖ¶з©Ңзҡ„жҜ”е–»гҖӮ
еҗҰеүҮеҹәзқЈйӮ„иғҪз”Ёд»Җйәјж–№ејҸйҖҸйҒҺжҲ‘еҖ‘жҠҠзҘӮиҮӘе·ұеӮійҒһзөҰеҲҘдәәпјҹжҠҠжҲ‘еҖ‘иҮӘе·ұзңӢдҪңжҳҜиҖ¶з©Ңзҡ„жҜ”е–»пјҢеҸҜд»Ҙжұ°йҷӨи«ҫж–Ҝеә•дё»зҫ©йӮЈзЁ®йҒҺеәҰйқҲж„ҸеҢ–иҖҢжЁЎзіҠдёҚжё…зҡ„ж„ҸиұЎпјҢд»ҘзӮәдёҠеёқд»ҘжҹҗзЁ®зҘһзҘ•зҡ„ж–№ејҸйҖҸйҒҺжҲ‘еҖ‘жөҒжәўеҲ°д»–дәәиә«дёҠпјҢеҚ»еҝҪз•ҘдәҶжҲ‘еҖ‘еҺҹжҳҜеҜҰйҡӣиҖҢе…·й«”ең°еӯҳеңЁж–јжӯ·еҸІжҷӮй–“дёӯгҖӮ
йҖҷзЁ®зҘһзҘ•зҡ„иҖ¶з©ҢеҲҶжөҒзҗҶи«–дёҰдёҚйңҖиҰҒд»»дҪ•еҖ«зҗҶеӯёеҹәзӨҺпјҢеҰӮжӯӨдёҖдҫҶпјҢжҲ‘жҳҜиӘ°гҖҒжҲ‘ж—Ҙеёёз”ҹжҙ»зҡ„жүҖиЎҢжүҖжҳҜпјҢж №жң¬йғҪи®Ҡеҫ—з„Ўй—ңз·ҠиҰҒгҖӮ
жҜҸеҖӢеҹәзқЈеҫ’зҡ„дёҖз”ҹйғҪжҮүи©ІжҲҗзӮәиҖ¶з©Ңзҡ„жҜ”е–»гҖӮзү§иҖ…жӣҙжҳҜеҰӮжӯӨпјҢеӣ зӮәзү§иҖ…еӨ§йғЁеҲҶзҡ„жҷӮй–“йғҪз”ЁдҫҶеҒҡиҖ¶з©Ңз”ҹе№іеҒҡйҒҺзҡ„дәӢгҖӮ
зү§йӨҠдәӢеҘүзҡ„жҒ°з•¶е®ҡзҫ©жҮү當еҰӮжӯӨеј·иӘҝпјҡи·ҹйҡЁиҖ¶з©Ңе°ұжҳҜдёҖзЁ®зү§йӨҠиЎҢеӢ•пјҢе°Өе…¶жҳҜиҰҒи·ҹйҡЁиҖ¶з©Ңиө°дёҠеҚҒеӯ—жһ¶зҡ„йҒ“и·ҜгҖӮ
✽✽✽
зү§йӨҠе·ҘдҪңзҡ„еҠӣйҮҸдҫҶжәҗпјҢд»ҘеҸҠиіҰдәҲзү§йӨҠе·ҘдҪңеҗ„зЁ®ж„Ҹзҫ©зҡ„ж ёеҝғз„Ұй»һпјҢе…ЁйғҪеңЁж–јжҜҸеӨ©еңЁз”ҹжҙ»дёӯе…·й«”ең°и·ҹйҡЁиҖ¶з©ҢпјҢи®“зҘӮеј•е°ҺжҲ‘еҖ‘иө°дёҠеҚҒеӯ—жһ¶зҡ„йҒ“и·ҜгҖӮ
еҰӮжӯӨдёҖдҫҶпјҢжҲ‘еҖ‘еҫ—д»ҘжҲҗзӮәиҖ¶з©Ңзҡ„жҜ”е–»пјҢдёҰе°ҮзҘӮеӮійҒһзөҰжҲ‘еҖ‘жүҖйҒҮиҰӢзҡ„дәәгҖӮдҝқзҫ…еңЁеҜ«зөҰе“Ҙжһ—еӨҡж•ҷжңғзҡ„жӣёдҝЎдёӯпјҢзү№еҲҘиӮҜе®ҡйҖҷдёҖй»һпјҢд»–иӘӘпјҡгҖҢиә«дёҠеёёеё¶и‘—иҖ¶з©Ңзҡ„жӯ»пјҢдҪҝиҖ¶з©Ңзҡ„з”ҹд№ҹйЎҜжҳҺеңЁжҲ‘еҖ‘иә«дёҠгҖӮ
еӣ зӮәжҲ‘еҖ‘йҖҷжҙ»и‘—зҡ„дәәжҳҜеёёзӮәиҖ¶з©Ңиў«дәӨж–јжӯ»ең°пјҢдҪҝиҖ¶з©Ңзҡ„з”ҹеңЁжҲ‘еҖ‘йҖҷеҝ…жӯ»зҡ„иә«дёҠйЎҜжҳҺеҮәдҫҶгҖӮгҖҚпјҲжһ—еҫҢеӣӣ10пҪһ11пјү
жІ’жңүд»»дҪ•дәӢзӯүеҗҢж–ји·ҹйҡЁеҹәзқЈгҖӮд»»дҪ•е·ҘдҪңжҢҮеҚ—гҖҒд»»дҪ•еҹәзқЈж•ҷйҒӢеӢ•жҲ–и¶ЁеӢўйўЁе°ҡгҖҒд»»дҪ•зү№е®ҡзҡ„жңҚдәӢй …зӣ®……е…ЁйғҪдёҚиғҪгҖӮ
然иҖҢпјҢдёҖж—ҰжҲ‘еҖ‘зҡ„з”ҹе‘Ҫй–Ӣе§Ӣй…ҚеҗҲиҖ¶з©Ңзҡ„з”ҹе‘ҪпјҢжҲ‘еҖ‘еңЁж•ҷжңғдәӢеӢҷдёҠеӨ§еҸҜеҗ‘иЁұеӨҡеҹәзқЈж•ҷйҒӢеӢ•йўЁжҪ®еҖҹйҸЎпјҢж“Үе„ӘдҪҝз”ЁпјҢд№ҹз„ЎеҰЁжҺЎз”Ёз®ЎзҗҶ委員жңғеҲ¶еәҰпјҢз”ҡиҮідҪҝз”ЁзңҒжҷӮжңүж•Ҳзҡ„е·ҘдҪңж—ҘзЁӢиЎЁпјҒ
еҲҘжҠҠи·ҹйҡЁеҹәзқЈжғіеҫ—еҫҲйӣЈгҖӮйӮЈдәӣдёҚйЎҳжҚЁе·ұиғҢиө·иҮӘе·ұеҚҒеӯ—жһ¶зҡ„дәәпјҢеҸҚиҖҢжңғзҷјзҸҫзү§йӨҠдәӢеҘүи®Ҡеҫ—жӣҙйӣЈгҖҒжӣҙз—ӣиӢҰгҖӮ
иҖ¶з©ҢиӘӘпјҡгҖҢеҮЎеӢһиӢҰж“”йҮҚж“”зҡ„дәәеҸҜд»ҘеҲ°жҲ‘йҖҷиЈЎдҫҶпјҢжҲ‘е°ұдҪҝдҪ еҖ‘еҫ—е®үжҒҜгҖӮжҲ‘еҝғиЈЎжҹ”е’Ңи¬ҷеҚ‘пјҢдҪ еҖ‘з•¶иІ жҲ‘зҡ„и»ӣпјҢеӯёжҲ‘зҡ„жЁЈејҸпјӣйҖҷжЁЈпјҢдҪ еҖ‘еҝғиЈЎе°ұеҝ…еҫ—дә«е®үжҒҜгҖӮеӣ зӮәжҲ‘зҡ„и»ӣжҳҜе®№жҳ“зҡ„пјҢжҲ‘зҡ„ж“”еӯҗжҳҜиј•зңҒзҡ„гҖӮгҖҚпјҲеӨӘеҚҒдёҖ28пҪһ30пјүйҖҷеҸҘи©ұеҗҢжЁЈйҒ©з”Ёж–јжҲ‘еҖ‘еҒҡзү§её«зҡ„иә«дёҠгҖӮ
е°ҚжҲ‘дҫҶиӘӘпјҢжҜҸдёҖеӨ©пјҢ當жҲ‘еҹ·иЎҢзү§иҖ…еҲҶе…§зҡ„е·ҘдҪңпјҢжҲ‘е°ұжҳҜи·ҹйҡЁиҖ¶з©Ңзҡ„дәәпјҢеӣ жӯӨпјҢе°ҚйӮЈдәӣиҲҮжҲ‘зӣёйҒҮзҡ„дәәдҫҶиӘӘпјҢжҲ‘е°ұжҳҜиҖ¶з©Ңзҡ„жҜ”е–»гҖӮиҖ¶з©Ңзҡ„жҜ”е–»жҠҠиҖ¶з©Ңзҡ„ж¬ҠиғҪиҲҮиҮЁеңЁеё¶е…Ҙд»–еҖ‘зҡ„з”ҹе‘ҪпјҢй–Ӣе§ӢйҒӢиЎҢгҖӮйҖҷе°ұжҳҜзү§йӨҠдәӢеҘүгҖӮ
жҲ‘дёҚйҒҺжҳҜдёҖж №з”ЁзҫҪжҜӣе’ҢзөІз·ҡеҒҡжҲҗгҖҒ模擬иңүиқЈжЁЈж…Ӣзҡ„жҜӣйүӨгҖӮ當жҲ‘жҜҸеӨ©и·ҹйҡЁиҖ¶з©ҢпјҢжҲ‘е°ұжҳҜеңЁзӮәдёҠеёқеҫ—дәәеҰӮйӯҡгҖӮиӘӘеҲ°еә•пјҢжҲ‘жҳҜд»Җйәје‘ўпјҹжҲ‘жҳҜдёҠеёқзҡ„йҮЈйӨҢгҖӮ
е°Һи®Җ
зү§иҖ…пјҢжҳҜдҪҚжңүж•…дәӢзҡ„зҘһеӯёе®¶
жўҒиҖҝзў©пјҲж Ўең’жӣёжҲҝеҮәзүҲзӨҫз·ЁијҜпјү
зү§иҖ…пјҢжҳҜжңүж•…дәӢзҡ„зҘһеӯёе®¶пјҢд»–иҰӘиҮӘеҮәзҸҫеңЁжҜҸдёҖеҖӢз”ҹе‘Ҫзҡ„иҷ•еўғпјӣд»–еңЁе ҙпјҢдҪҝеҫ—дәәеҸҜд»ҘзңӢиҰӢиҖ¶з©Ңзҡ„еңЁе ҙпјӣйӮЈжҲ–иЁұжҳҜеңЁзӮәи‘—е·ІеҗҢеұ…з”ҹеӯҗзҡ„з”·еҘіиӯүе©ҡзҡ„жҷӮеҲ»пјҢжҲ–иЁұжҳҜжҺўжңӣдёҖдҪҚе°ҮиҰҒиө°е…Ҙжӯ»дәЎзҡ„е№ҙй•·е§ҠеҰ№пјӣзӮәдёҖдҪҚеҖ–еӯҳж–је…¬зүӣж’һж“Ҡзҡ„зүӣд»”ж–Ҫжҙ—пјӣзӮәдёҖдҪҚеӣ ж•…иў«иӯҰж–№иҝҪж“ҠпјҢиҖҢеңЁйҗөи»ҢдёҠиў«зҒ«и»Ҡж’һжӯ»зҡ„йқ’е°‘е№ҙиҲүиҫҰе–ӘзҰ®пјӣеңЁз”ўжҲҝпјҢйҷӘдјҙдёҖеҖӢ家еәӯз”ҹдёӢиғҺжӯ»и…№дёӯзҡ„дёғеҖӢжңҲеӨ§иғҺе…’пјҺпјҺпјҺ
1934е№ҙзҡ„еҫ·еңӢиҠ¬ж №з“Ұеҫ—пјҲFinkenwaldeпјүпјҢе№ҙиј•зҡ„зҘһеӯёе®¶жҪҳйңҚиҸҜжӯЈеңЁең°дёӢзҘһеӯёйҷўиЁ“з·ҙи‘—иӘҚдҝЎж•ҷжңғжңӘдҫҶзҡ„зү§иҖ…пјӣ然еҫҢпјҢжҳҜ1983е№ҙпјҢдёҖжңҲеӣӣж—Ҙзҡ„дёӢеҚҲпјҢдёҖдҪҚдҫҶиҮӘеҠ е·һзҡ„з”·дәәй–Ӣи‘—и»ҠпјҢијүи‘—еҰ»еӯҗе’ҢдёүеҖӢеӯ©еӯҗжҠөйҒ”зҫҺеңӢи’ҷеӨ§жӢҝе·һпјҢеңЁзӢӮжҡҙзҡ„йўЁйӣӘдёӯпјҢеұ•й–ӢдёҖж®ө嶄新зҡ„з”ҹжҙ»гҖӮжҲ–иҖ…пјҢжҳҜ2013е№ҙзҡ„еҸ°зҒЈж–°еҢ—еёӮпјҢеҜ’еҶ·иҖҢдёӢи‘—йӣЁзҡ„жҹҗеҖӢеӨңжҷҡпјҢдёҖдҪҚз”·еӯҗеңЁж•ҷжңғеё¶й ҳиЁұеӨҡдәәдёҖиө·зҰұе‘ҠгҖӮ
дёҠиҝ°зҡ„йҖҷдәӣдәәжңүз”ҡйәје…ұеҗҢй»һе—Һпјҹжңүзҡ„пјҢдё»и§’йғҪжҳҜжңҚдәӢиҖ¶з©ҢеҹәзқЈзҡ„зү§иҖ…гҖӮзү§иҖ…пјҢжңүеҸҜиғҪжҳҜйҖҷеҖӢдё–з•ҢдёҠжңҖиүұеӣ°зҡ„е·ҘдҪңд№ӢдёҖгҖӮдёҖж–№йқўпјҢиЁұеӨҡдәәиӘҚзӮәйҖҷжҳҜжңҖзҘһиҒ–гҖҒе…Ёдё–з•ҢжңҖйҮҚиҰҒзҡ„е·ҘдҪңд№ӢдёҖпјҢеӣ зӮәжҳҜиҰҒдҪңйқҲйӯӮзҡ„зү§дәәпјҢд№ҹеҝ…й ҲжңүдҫҶиҮӘдёҠеёқзҡ„жё…жҘҡе‘јеҸ¬гҖӮ然иҖҢпјҢйҖҷеӨ§жҰӮд№ҹжҳҜдёҖд»ҪеЈ“еҠӣжңҖеӨ§зҡ„е·ҘдҪңгҖӮиЁұеӨҡдәәжңҹеҫ…зү§иҖ…жҳҜй ҳе°ҺиҖ…пјҢжҳҜйҶ«жІ»иҖ…пјҢжҳҜз®ЎзҗҶиҖ…пјҢиҰҒжңғи¬ӣйҒ“гҖҒжҺўиЁӘгҖҒеӮізҰҸйҹігҖҒеӨ§жңүиғҪеҠӣзҡ„зҰұе‘Ҡпјӣз°Ўе–®ең°иӘӘпјҢе№ҫд№Һе°ұжҳҜе…ЁиғҪгҖӮйҷӨжӯӨд№ӢеӨ–пјҢзү§йӨҠйҒҺзЁӢиҲҮжңғзңҫгҖҒиҲҮиҮӘиә«з”ҹе‘Ҫзҡ„жҗҸй¬ҘпјҢиҲҮе…¶д»–зү§иҖ…зҡ„зӣёиҷ•пјҢдёҚиў«дәҶи§Јзҡ„еӯӨзҚЁж„ҹгҖҒдәӢеҘүжҲҗжһңзҡ„дёҚзӣЎзҗҶжғіпјҢеҸҲеҸҜиғҪдҪҝиЁұиЁұеӨҡеӨҡзҡ„зү§иҖ…дёӯйҖ”иҖҢе»ўпјҢеҚҠйҖ”йҷЈдәЎгҖӮжҲ–иҖ…з№јзәҢеүҚиЎҢпјҢиә«дёҠеҚ»жҳҜж»ҝеёғеӮ·з—•гҖӮ
еңЁгҖҠзү§йӨҠзҡ„и—қиЎ“гҖӢйҖҷжң¬зҚІеҫ—з•ўеҫ·з”ҹзү§её«жҺЁи–Ұзҡ„жӣёдёӯпјҢдҪңиҖ…еӨ§иЎӣвҖ§йҹ“жЈ®пјҲDavid HansenпјүпјҢеҗҢжЁЈйқўе°Қи‘—йҖҷдәӣжҺҷжүҺгҖӮд»–жӯЈжҳҜйӮЈдҪҚж–ј1983е№ҙдёҖжңҲеӣӣж—ҘдёӢеҚҲжҠөйҒ”и’ҷеӨ§жӢҝзҡ„еҠ е·һз”·еӯҗгҖӮзҘһеӯёйҷўз•ўжҘӯеҫҢпјҢд»–еҲ°зҫҺеңӢи’ҷеӨ§жӢҝй„үй–“еҗҢжҷӮзү§йӨҠе…©й–“е°ҸеһӢж•ҷжңғпјҢе°Үиҝ‘дәҢеҚҒијүд№ӢеҫҢпјҢй ҶеҫһзҘһзҡ„её¶й ҳпјҢеҶҚйҒ·иҮідҝ„дәҘдҝ„е·һзҡ„иҫӣиҫӣйӮЈжҸҗзү§йӨҠеӨ§еһӢж•ҷжңғгҖӮйӮЈйәјпјҢд»–жҳҜеҰӮдҪ•иө°йҒҺйҖҷжЁЈзҡ„жҺҷжүҺпјҢеҜ«еҮәдәҶгҖҠзү§йӨҠзҡ„и—қиЎ“гҖӢйҖҷжң¬иў«иЁұеӨҡи®ҖиҖ…иӘҚзӮәиғҪеӨ жҢҪж•‘зү§иҒ·зҡ„жӣёе‘ўпјҹ
йҹ“жЈ®зү§её«еҫһдёҖеҖӢд№ҚзңӢд№ӢдёӢжңҖз°Ўе–®пјҢеҚ»жңҖж №жң¬зҡ„е•ҸйЎҢй–Ӣе§ӢгҖӮиҲүзӣ®еӣӣжңӣпјҢзү§иҖ…жңүеҫҲеӨҡиіҮжәҗгҖҒеҫҲеӨҡжүӢеҶҠеҺ»жүҫеҲ°иҮӘе·ұи©ІеҒҡд»ҖйәјгҖӮгҖҢ然иҖҢжҲ‘當жҷӮдёҚеғ…дёҚиӘҚиӯҳиҮӘе·ұпјҢдёҚзҹҘйҒ“иҮӘе·ұжҳҜиӘ°пјҢд№ҹдёҚжҳҺзҷҪиҮӘе·ұзӮәд»ҖйәјжҮүи©ІеҺ»еҒҡйӮЈдәӣи©ІеҒҡзҡ„дәӢгҖӮжҲ‘д№ҹдёҚзҹҘйҒ“йҖҷдәӣи©ІеҒҡзҡ„дәӢиҰҒжҖҺжЁЈиҲҮжҲ‘еҖӢдәәзҡ„е‘јеҸ¬дә’зӣёй…ҚеҗҲгҖҒеҚ”иӘҝдёҖиҮҙгҖӮгҖҚпјҲ第дёҖз« пјҢгҖҲй–Ӣз«ҜгҖүпјүеҺҹдҫҶпјҢгҖҢзү§иҖ…еҲ°еә•жҳҜиӘ°пјҹгҖҚйҖҷеҖӢй—ңйҚөзҡ„е•ҸйЎҢеҝ…й Ҳе…Ҳеҫ—еҲ°и§ЈжұәпјҢеҗҰеүҮеҶҚеӨҡзҡ„зү§йӨҠе·ҘдҪңжүӢеҶҠйғҪдёҚиғҪжҸҗдҫӣ幫еҠ©гҖӮ
гҖҖгҖҖзҘһеӯёпјҢ幫еҠ©зү§иҖ…зҹҘйҒ“иҮӘе·ұжҳҜиӘ°
гҖҖгҖҖйҹ“жЈ®зү§её«зҷјзҸҫпјҢзҘһеӯёжӣёзұҚгҖҒиҒ–з¶“з ”з©¶иҲҮж•ҷжңғжӯ·еҸІзҡ„дҪңе“ҒпјҢиғҪеӨ 幫еҠ©зү§иҖ…йҮҗжё…йҖҷеҖӢжңҖж №жң¬зҡ„е•ҸйЎҢгҖӮд»–жңүж®өи©ұиӘӘеҫ—жҘөзӮәжңүи¶ЈпјҡгҖҢжҲ‘ијӘжөҒй–ұи®ҖиЁұеӨҡдёҚеҗҢеӯёй–Җзҡ„жӣёзұҚгҖӮйҖҷдәӣжӯЈзөұзҘһеӯёз§‘зӣ®зҡ„жӣёзұҚжІ’жңүж•ҷжҲ‘жҖҺйәјеҒҡзү§йӨҠе·ҘдҪңпјҢдҪҶеҚ»еңЁдҫӢеёёе·ҘдҪңзҡ„иҒ·еӢҷдёҠдҪҝжҲ‘зҚІзӣҠиүҜеӨҡгҖӮжҲ‘зҷјзҸҫиҠұдёҖж•ҙеӨ©жҷӮй–“и®ҖдёҠдёүеҚҒй Ғе·ҙзү№пјҲKarl Barthпјүзҡ„гҖҠж•ҷжңғж•ҷзҫ©еӯёгҖӢпјҲDogmaticsпјүпјҢе°Қзү§йӨҠе·ҘдҪңзҡ„幫еҠ©йҒ з”ҡж–јй–ұи®Җзҷҫй Ғд»ҘдёҠзҡ„зү§йӨҠе·ҘдҪңжҢҮеҚ—гҖӮгҖҚ
еӣ зӮәиӢҘиҰҒеӣһзӯ”гҖҢзү§иҖ…жҳҜиӘ°гҖҚпјҢеҝ…然иҰҒиҝҪе•ҸгҖҢзү§иҖ…жүҖжңҚдәӢзҡ„дёҠеёқжҳҜиӘ°пјҹгҖҚжҸӣеҸҘи©ұиӘӘпјҢзү§иҖ…зҡ„иә«еҲҶиӘҚеҗҢпјҢжңҖзөӮеҝ…然жҳҜй—ңд№ҺдёҠеёқжҳҜиӘ°пјҢд№ҹе°ұжҳҜдёҠеёқи«–жҲ–зҘһи«–зҡ„е•ҸйЎҢгҖӮж–јжҳҜжҲ‘еҖ‘жүҚиғҪеӨ жҳҺзҷҪпјҢжјўжЈ®зү§её«д»ҘдёҠжүҖиӘӘйҖҷж®өи©ұзҡ„ж„Ҹзҫ©пјҡйҖҸйҒҺзҘһеӯёпјҢжҲ–иҖ…иӘӘжҳҜж•ҷзҫ©еӯёпјҢйҮҚж–°жҺўзҙўжҲ–йҮҗжё…дёҠеёқи«–зҡ„е•ҸйЎҢпјҢз”ұжӯӨжүҚиғҪйҮҗжё…зү§иҖ…зҡ„иә«еҲҶиӘҚеҗҢгҖӮеҸҜд»ҘйҖҷйәјиӘӘпјҡзү§иҖ…еҝ…й ҲдёҚж–·жҙ»еңЁгҖҢиӘҚиӯҳиҮӘе·ұгҖҚе’ҢгҖҢиӘҚиӯҳдёҠеёқгҖҚзҡ„иҫҜиӯүе’Ңе°Қи©ұ當дёӯпјҢзңҹжӯЈиӘҚиӯҳдёҠеёқзҡ„зү§иҖ…пјҢдёҚж–·жҖқиҖғдёҠеёқжҳҜиӘ°зҡ„зү§иҖ…пјҢжүҚиғҪжҳҺзҷҪиҮӘе·ұжҳҜиӘ°гҖӮеӣ жӯӨдҪңиҖ…иӘӘпјҢдёҠеёқзҡ„еӯҳеңЁжҳҜзү§йӨҠ當дёӯзҡ„зңҹжӯЈиӯ°йЎҢпјӣдёҚжҳҜгҖҢдёҠеёқеӯҳдёҚеӯҳеңЁгҖҚпјҢиҖҢжҳҜгҖҢдёҠеёқжҳҜиӘ°гҖҚпјҢгҖҢзҘӮеңЁе“ӘиЈЎгҖҚпјҢйҖҷжҳҜжңҖй—ңйҚөзҡ„иӯ°йЎҢпјҲ第дёғз« пјҢгҖҲзҰұе‘ҠгҖүпјүгҖӮ
жјўжЈ®зү§её«д№ҹеңЁдёҖдҪҚзҘһеӯёе®¶зҡ„иә«дёҠпјҢжүҫеҲ°жңҖй—ңйҚөзҡ„幫еҠ©пјҢйӮЈдҪҚзҘһеӯёе®¶жҳҜйӣІж јзҲҫгҖӮ
з”ЁжңҖз°Ўе–®зҡ„и©ұдҫҶиӘӘпјҢйӣІж јзҲҫиӘҚзӮәжҲ‘еҖ‘еҸҜд»ҘиӘҚиӯҳдёҠеёқпјҢжҳҜеӣ зӮәдёҠеёқе®ҡж„Ҹеҗ‘жҲ‘еҖ‘е•ҹзӨәзҘӮиҮӘе·ұпјӣиҖҢе°ҮзҘӮзҡ„еӯҳжңүпјҲbeingпјүйЎҜжҳҺпјҢдҪҝжҲ‘еҖ‘еҫ—д»ҘиӘҚиӯҳзҘӮдёҰдё”иҲҮзҘӮе»әз«Ӣй—ңдҝӮзҡ„пјҢжҳҜзҘӮиҮЁеҲ°дәәй–“зҡ„зҚЁзү№дәӢ件пјҢе°ұжҳҜеҹәзқЈзҡ„йҒ“жҲҗиӮүиә«пјҡгҖҢеңЁйҒ“жҲҗиӮүиә«иЈЎпјҢдёҠеёқеӣ жҲҗзӮәдәәиҖҢиҮЁиҝ‘дәәйЎһпјҢз”Ёдәәзҡ„иӘһиЁҖеҗ‘дәәиӘӘи©ұпјҢиҖҢдҪҝе…¶иҮӘиә«иҲҮдәәйЎһзӣёй—ңпјҢиҖҢдҪҝзҘӮиғҪиў«жҲ‘еҖ‘жҖқиҖғгҖӮгҖҚпјҲгҖҠдёҠеёқдҪңзӮәдё–з•Ңзҡ„еҘ§зҘ•гҖӢпјүжӯЈжҳҜеңЁжӯӨж„Ҹзҫ©дёҠпјҢиҖ¶з©ҢеҹәзқЈжҲҗдәҶдёҠеёқзҡ„жҜ”е–»пјҢжҠҠи¶…и¶ҠдәәзҗҶи§Јзҡ„дёҠеёқиЎЁжҳҺдәҶеҮәдҫҶгҖӮжјўжЈ®зү§её«еңЁз•¶дёӯзңӢеҲ°дәҶйЎһжҜ”зҡ„еҸҜиғҪпјҡгҖҢиҖ¶з©Ңзҡ„ж•…дәӢе°ұжҳҜдёҠеёқзҡ„жҜ”е–»пјҢеӣ зӮәиҖ¶з©ҢжҳҜеҸҜиҰӢзҡ„дәәеӯҗпјҢиҖҢдёҠеёқеүҮжҳҜдёҚеҸҜиҰӢзҡ„йқҲгҖӮиҖ¶з©Ңзҡ„з”ҹе№іе°ұжҳҜдёҠеёқзҡ„ж•…дәӢпјҢд№ҹжҳҜдёҠеёқзҡ„ж„ӣпјҢ當жҲ‘еҖ‘иҒҪиҰӢдёҰдё”зӣёдҝЎиҖ¶з©Ңзҡ„ж•…дәӢжҷӮпјҢдёҠеёқе°ұиҮЁеңЁжҲ‘еҖ‘當дёӯдәҶгҖӮпјҺпјҺпјҺиҖ¶з©ҢжҳҜдёҠеёқзҡ„е–»иұЎпјҢзҘӮд»ҘйҖҷзЁ®ж–№ејҸе°ҮдёҠеёқеё¶зөҰжҲ‘еҖ‘гҖӮйҖҷжҳҜеҗҰиЎЁзӨәпјҢзү§иҖ…д№ҹеҸҜд»Ҙж №ж“ҡд»–еҖ‘и·ҹйҡЁиҖ¶з©Ңзҡ„зЁӢеәҰж·ұж·әпјҢиҖҢеӨҡеӨҡе°‘е°‘е°ҮиҮӘе·ұиҪүи®ҠжҲҗиҖ¶з©ҢеҹәзқЈзҡ„е–»иұЎпјҢдёҰеӣ жӯӨжҠҠиҖ¶з©Ңеё¶еҲ°йӮЈдәӣиҲҮд»–еҖ‘зӣёйҒҮзҡ„дәәйқўеүҚпјҹгҖҚпјҲ第дёҖз« пјҢгҖҲй–Ӣз«ҜгҖүпјүгҖӮ
еңЁйӣІж јзҲҫзҡ„дёҠеёқи«–дёӯпјҢжјўжЈ®зү§её«жүҫеҲ°дәҶзү§иҖ…зҡ„иә«еҲҶиӘҚеҗҢд№ӢжүҖеңЁгҖӮиҖ¶з©ҢжҳҜдёҠеёқзҡ„жҜ”е–»пјҢжҠҠдёҠеёқиЎЁжҳҺеҮәдҫҶпјҢи—үжӯӨжҲ‘еҖ‘иӘҚиӯҳдёҠеёқпјӣиҖҢзү§иҖ…еүҮжҳҜиҖ¶з©Ңзҡ„жҜ”е–»пјҢжҠҠиҖ¶з©ҢиЎЁжҳҺеҮәдҫҶпјҢи—үжӯӨжҲ‘еҖ‘зңӢиҰӢдәҶиҖ¶з©ҢгҖӮ
з”ұжӯӨпјҢжҲ‘еҖ‘д№ҹжҳҺзҷҪдҪңиҖ…зӮәдҪ•иҰҒиӘӘжң¬жӣёжҳҜй—ңж–јж•ҳдәӢпјҢжҳҜй—ңж–јд»–зҡ„з”ҹе‘Ҫж•…дәӢпјҢеӣ зӮәжҜ”е–»жӯЈжҳҜе…·й«”зҡ„ж•ҳдәӢпјҢдёҚжҳҜжҠҪиұЎзҡ„и§ҖеҝөпјҢд№ғжҳҜжңүиЎҖжңүиӮүгҖҒеә§иҗҪж–је…·й«”жҷӮз©әдёӯзҡ„пјӣеӣ жӯӨпјҢжңүдәӣзүҮж®өгҖҒз‘ЈзўҺгҖҒеҮәд№Һж„ҸеӨ–пјҢеҚ»жҳҜзңҹеҜҰпјҢж·ұе…Ҙз”ҹе‘Ҫзҡ„жҜҸдёҖеұӨйқўгҖӮ當зү§иҖ…з”ЁиҮӘе·ұзҡ„з”ҹе‘ҪиёҸдёҠеҚҒжһ¶зҡ„йҒ“и·ҜпјҢд»–е°ұжҲҗдәҶиҖ¶з©Ңзҡ„жҜ”е–»гҖӮ
д№ҹиЁұеҸҜд»ҘйҖҷйәјиӘӘпјҢзү§иҖ…пјҢжҳҜжңүж•…дәӢзҡ„зҘһеӯёе®¶пјҢд»–иҰӘиҮӘеҮәзҸҫеңЁжҜҸдёҖеҖӢз”ҹе‘Ҫзҡ„иҷ•еўғпјӣд»–еңЁе ҙпјҢдҪҝеҫ—дәәеҸҜд»ҘзңӢиҰӢиҖ¶з©Ңзҡ„еңЁе ҙпјӣйӮЈжҲ–иЁұжҳҜеңЁзӮәи‘—е·ІеҗҢеұ…з”ҹеӯҗзҡ„з”·еҘіиӯүе©ҡзҡ„жҷӮеҲ»пјҢжҲ–иЁұжҳҜжҺўжңӣдёҖдҪҚе°ҮиҰҒиө°е…Ҙжӯ»дәЎзҡ„е№ҙй•·е§ҠеҰ№пјӣзӮәдёҖдҪҚеҖ–еӯҳж–је…¬зүӣж’һж“Ҡзҡ„зүӣд»”ж–Ҫжҙ—пјӣзӮәдёҖдҪҚеӣ ж•…иў«иӯҰж–№иҝҪж“ҠпјҢиҖҢеңЁйҗөи»ҢдёҠиў«зҒ«и»Ҡж’һжӯ»зҡ„йқ’е°‘е№ҙиҲүиҫҰе–ӘзҰ®пјӣеңЁз”ўжҲҝпјҢйҷӘдјҙдёҖеҖӢ家еәӯз”ҹдёӢиғҺжӯ»и…№дёӯзҡ„дёғеҖӢжңҲеӨ§иғҺе…’пјҺпјҺпјҺ
гҖҢжҲ‘жЁЎд»ҝиҖ¶з©ҢпјҢе°ұеғҸзҫҪжҜӣе’Ңз·ҡй ӯзәҸзөҗзҡ„еҒҮи …йҮЈйӨҢжЁЎд»ҝж°ҙйқўдёҠзҡ„иңүиқЈгҖӮ然иҖҢ當жҲ‘еңЁз”ҹе‘Ҫзҡ„жҜҸдёҖеӨ©иЈЎеҺ»и·ҹйҡЁиҖ¶з©ҢпјҢжҲ‘е°ұжҳҜеңЁдҪңдёҠеёқзҡ„жјҒеӨ«пјҢзӮәдёҠеёқйҮЈдәәгҖӮжӯёж №з©¶жҹўпјҢжҲ‘иҮӘе·ұе°ұжҳҜйҮЈйӨҢгҖӮгҖҚйҮЈйӨҢпјҢдёҚжҳҜеңЁзү§иҖ…д»ҘеӨ–зҡ„жҹҗзү©пјҢйҮЈйӨҢпјҢе°ұжҳҜзү§иҖ…иҮӘе·ұгҖӮжҲ‘еҖ‘з„Ўжі•йҖғйҒҝйҖҷ件дәӢпјӣдёҚз®Ўзү§йӨҠзҡ„дәәжҳҜеҚҒеҖӢйӮ„жҳҜдёҖзҷҫеҖӢгҖҒдёҖеҚғеҖӢпјҢиӢҘиҰҒзңҹжӯЈжҠҠдәәеё¶еҲ°зҘһзҡ„йқўеүҚпјҢдҪ еҝ…й ҲдҪҝз”ЁиҮӘе·ұгҖӮйҖҸйҒҺдҪ зҡ„еңЁе ҙпјҢйҖҸйҒҺдҪ дёҖиј©еӯҗз”ҹжҙ»зҡ„жҜҸдёҖеҖӢзүҮж®өпјҢдҪ жҠҠдёҠеёқеё¶еҲ°дәәзҡ„йқўеүҚгҖӮ
еғ…д»ҘжӯӨж–ҮпјҢзҚ»зөҰжҜҸдёҖдҪҚзү§иҖ…пјҢиҲҮеҚіе°ҮжҲҗзӮәзү§иҖ…пјҢжҲ–жҳҜиҲҮзү§иҖ…еҗҢиЎҢзҡ„дәәгҖӮ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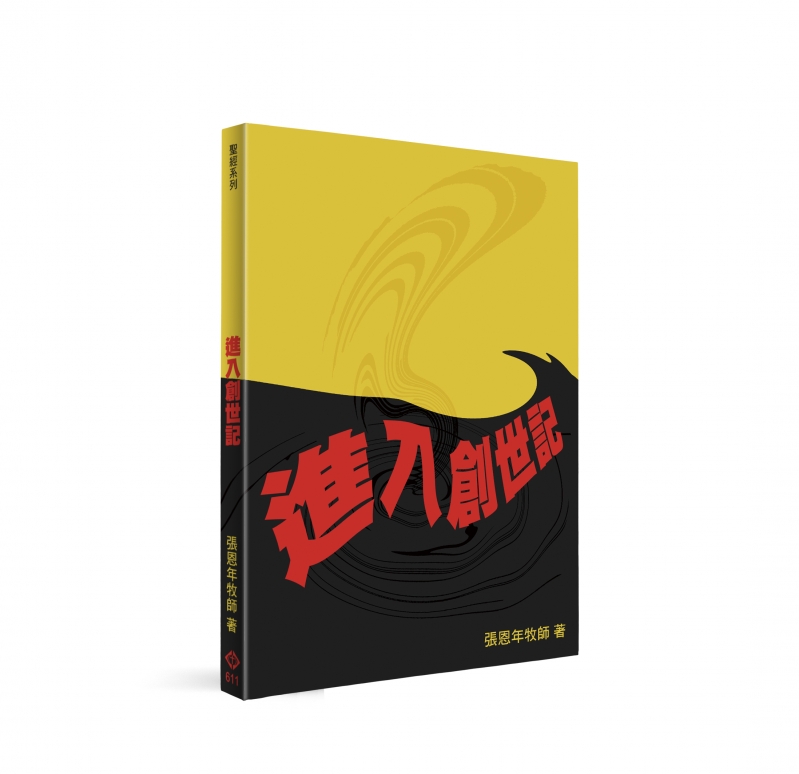
.png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