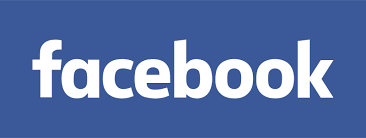「尊貴的法王,我是把兒童從A點移到B點的人。」我從未如此謙卑過。
老師說,奴隸制已隨美國解放宣言而終結了。真的是這樣嗎?
今日,有超過2700萬的人,在世界的各個角落被奴役著,
每年,大約有80萬名新的受害者送到黑暗地獄……
作者原是珍的沉溺(Jane’s Addiction)樂團主唱派瑞(Perry Farrell)的好友,也是這個樂團的創意策劃、經紀人。在度過瘋狂、無意義的浪子生活後,他決定用音樂來幫助世人,也就是進行「禧年計畫」,作者稱為「以音樂帶來和平」。
這個計畫的主要目的,是要在一段時間內重整事物運作,幫助受苦的人們重新找到生命意義,重燃我們人類本為一體的希望意識。在禧年,所有不平等、憐憫心都不復存在。沒有人會尋求幫助,也沒有人會以傳統觀念來提供「幫助」——因為沒有任何人會陷於需要別人幫助的境地。一旦我們進入無不平等的國度,我們就能自由地愛與被愛。
於是,作者決定深入柬埔寨、拉丁美洲、緬甸、蘇丹、伊拉克、以色列等絕惡之地,假冒嫖客深入妓女戶蒐集證據,冒險救援被國際人口販子以槍、毒和黑錢控制的可憐孩童與雛妓。直到取得可靠的證詞與證據,再協同國際機構的壓力,迫使當地政府採取行動,救出少女,並送入婦女援助及保護機構。
這份工作只有微薄的酬勞,卻必須承擔生命危險。在柬埔寨救出第一批少女後,立刻被勢力強大的黑道追殺;在厄瓜多爾落入陷阱,以致必須在槍林彈雨中狂奔、東躲西藏;在取得證人證物前,必須克制慾望與被下藥的風險;以及沒有女朋友,因為沒有人可以忍受他的行業內容。
一九九九年,高達1700萬人連署呼籲G8富國廢止第三世界國家國際債務,參與的搖滾界明星包括珍的沉溺主唱派瑞、著名的搖滾歌手與政治行動者Bono(U2樂團主唱)、鮑伯˙葛魯多福(The Boomtown Rats樂團主唱)。 作者也與瑞奇˙馬汀計畫到喜馬拉雅山拜見達賴喇嘛,請他在一系列公益廣告中代言,讓兒童警覺人口販運的陷阱。
「以音樂帶來和平」不再是口號;相信沒有奴隸制、貧窮與壓迫的烏托邦不是幼稚──只要我們不孤軍奮戰。
本書特色
深入報導柬埔寨、蘇丹、拉丁美洲、緬甸、中東等絕惡之地的妓女戶、黑幫叢林,冒險搜證以解放受害者。
場景和文字裡的悲憫綜合了《黑暗之心》、《殺戮戰場》、《貧民百萬富翁》和《沉靜的美國人》,而大開眼界的震撼更甚於閱讀《項塔蘭》!
如果您喜愛閱讀《三杯茶》,這本書更加不容錯過!
人權運動者,運動理念深受禧年及赦免債務、解放奴隸的古老律法啟發。柯恩一直致力於推展現代禧年運動,讓世界各地都能赦免債務、解放奴隸。因對抗人口販運,使柯恩受到洛杉磯政府的表揚。他在尼加拉瓜、以色列、埃及、厄瓜多爾、伊拉克、柬埔寨、緬甸等地執行國際任務的過程中擔任臥底密探,並且就他了解的內幕來評價奴隸制現象。他曾榮獲二次大戰紀念基金會∕不朽的牧師基金會(World WarⅡMemorial Foundation/the Immortal Chaplains)、2008年人道獎(Prize for Humanity),也曾因公共服務的貢獻榮獲美國國會的優異獎(Certificate of Merit)。柯恩目前定居於加州,繼續運用特殊作戰模式,在他的故鄉與海外執行奴隸救援任務。
克莉絲汀.巴克利(Christine Buckley)
生於紐約,畢業於波士頓學院。她的旅行足跡遍及五大洲,而且讓她學會了修剪羊毛、種稻、在沒有GPS定位裝置的情況下駕駛船隻、編輯嚴肅的國營報紙。克莉絲汀為《洛杉磯周刊》封面故事撰寫亞倫.柯恩的報導,入圍2008年洛杉磯記者俱樂部與瑪姬獎(L.A. Press Club and Maggie Award finalist)。同時,她也供稿給美國國家公共廣播電台的周末版(NPR’s Weekend Edition)、《紐約時報》、俄國的新聞周刊、潮流電視台與佛羅里達公共廣播電台,並因為為佛羅里達公共廣播電台製作的新聞,而獲得美聯社的獎項。克莉絲汀目前住在巴黎,打算在2009年重返東南亞參與服務人口販運受害者的工作。
Allez! Allez! Allez!
在回家的飛機上聆聽納凡諾的演奏,腦海中湧現過去十年的歲月,我打從心底哭了。九一一讓我想起那些無意義死去的每一位朋友。我大學時代的朋友科琳在二十多歲時死於用藥過量;嗆辣紅椒的希勒爾.斯洛伐克,這位即使連續狂歡了四、五天都還有辦法做出令你靈魂哭泣的音樂人,也死於用藥過量。科特.柯本在連續吸毒一星期後,舉槍射擊了自己的腦袋。
四年來,我不斷告訴自己:透過愛與音樂的共同語言,世界和平是垂手可得的,所以我不斷在詮釋禧年。然而,此刻,我發現有太多事情不可掌握。我的禧年之夢尚未失落,但我必須找出讓它實現的新方向。免除債務是已踏出的第一步。我記得在那場運動中,一些音樂家對那些「不酷」的政治人物有所批評,而U2波諾說了一些提醒的話。他說,我們必須和所有想幫助我們解決貧窮問題的人合作,不論他們有多麼「不酷」。
我們離洛杉磯愈來愈近了,我把有關禧年之夢的所有事情想過一遍後,我已做好心理建設來面對迫在眉睫的事。我必須暫時將崇高的任務擺在一邊,先照顧爸爸——這是我不斷努力在夢想與孝道之間取得平衡的新階段。我們落地時,我已順從了必須立刻照顧父親的命運。爸爸的狀況正在惡化,我必須陪他。不過,我心裡已開始在準備計畫下一個大目標,將我一直努力想實現的所有方向結合在一起。我在蘇丹時已了解,即使我只是個小人物,還是能創造出一些改變來造福人類。我不需要透過搖滾明星或禧年巡迴音樂會來促成改變。我只需要幫助人們看到我所看到的——我們每個人都擁有行動的能量,來對抗那使我們的社會墮落、奴役他人的強大力量。
我思索著海星的寓言。
有天早上,一個男人走在退潮的海灘上,看見一個女人拾起被沖到海灘上的海星,然後把牠們丟回海裡,而且每次只丟一隻。他走過去問她在做什麼。
「我在給這些海星一個機會。」她說:「如果我什麼也不做,牠們就會死。」
「是啊!可是,被沖上這個海灘或其他海灘的海星數以千計,」他說:「每天都是如此。事情本來就這樣。你不可能改變什麼的。」
這女人把另一隻海星丟回海裡,微笑地對男人說:「沒錯,我剛剛改變了那一隻的未來。」
我從紐約回來幾星期後,爸爸嚴重中風,被送進醫院。亞瑟和瑞絲隨後幾個星期飛回來,接著照顧康復期的爸爸。我們不確定他是否還能再走路或講話,護士們注視著我們,問:「接下來,你們打算給父親使用哪一種更昂貴的照顧器材?」
我們望著彼此,討論該如何作選擇。如果我不留在爸爸身邊照顧他,就得請個護士到家裡,這是我們的最後一個辦法。亞瑟有太太、七個小孩與幾十個病人要照顧。瑞絲家裡有老公、五個女兒和一條叫做露西的狗。我才剛失去派瑞那邊的工作,所以我有空。我退掉威尼斯的公寓,把東西搬回加州科斯塔梅薩、我童年時期的臥室。
*
幾個月過去了。我沒有打電話給派瑞,他也沒有打給我。我每天都很早起床,為爸爸做早餐,幫他換床單和衣服,陪他走路或用輪椅推他到廚房的飯桌,陪他吃每天都要吃的薄煎餅。我認為派瑞和我都覺得自己被對方遺棄了。他又發行了一張個人專輯,而且即將要與復出的珍的沉溺的其他團員錄另一張專輯。他的名字再度廣為人知,而我坐在郊區的家裡,用湯匙餵食曾經虐待我、卻也是我在世上最愛的人——我的父親。
位於佛洛里達州一家小雜誌的記者跟我聯繫,訪問我在蘇丹對抗奴隸制的行動。那篇報導登出後,我在美國反奴隸組織的熟人告訴我,瑞奇.馬汀想和我見面。瑞奇自己創了一個慈善基金會,致力於解救可能終身被債務奴役的印度兒童。
瑞奇手下的協調員米雷耶.布拉沃和我聯繫。不到幾星期(這段時間內我都在爸爸身邊用電腦工作),我們就在瑞奇馬汀基金會的羽翼下發起了一項新運動——人人為兒童(People for Children)——保護脆弱的兒童,讓他們免於落入人口販子之手。
幾個月後,瑞奇問我是否能聯繫達賴喇嘛,請他在一系列公益廣告中代言,讓兒童警覺人口販運的陷阱。在陪伴爸爸的陰鬱下日益枯萎的我,一直夢想回蘇丹,而如今,有位超級知名人士樂於從事的工作,遠比解救印度及拉丁美洲奴隸兒童更有影響力。我當然有興趣。
我應邀到衝浪者療癒晚會幫助自閉症兒童,沒想到竟和派瑞不期而遇。突然看到將近一年沒講過隻字片語的密友,感覺真的很怪。我們之前交換過彼此的手機號碼,卻幾乎完全失聯。不過,我告訴派瑞我為瑞奇.馬汀做的公益廣告時,心裡還是期待他能為我開心,但我看到他露出某種被背叛與輕蔑的神情。瑞奇.馬汀是流行音樂明星,不是另類搖滾之神。
然而,我思念他,而且在喝了一杯紅酒之後坦白這麼對他說。開始聊天後,我發現自己沉陷於我們一起衝浪與閱讀的日子裡。「嘿,派瑞,」我坦蕩地直視著他說:「你必須為了你自己去蘇丹看看。我認為你可以利用你的音樂連結那些人。」
他說:「要出遠門很困難。不過,我會試試看。」我們再度擁別。我知道他會信守諾言。
隔天早上,我繼續進行人人為兒童的任務。經過幾個月對西藏的運動者、知識份子及官員的遊說之後,我終於獲得達賴喇嘛的特使洛地嘉日的許可。法王同意參加公益廣告的計畫。我太高興了。瑞奇叫我前往印度拍攝影片。他和他的團隊會比我晚一星期到。
我大清早就抵達德里。離開飛機場時,我注意到的第一件事就是安全門外面的混亂景象。那時天色還沒亮,卻瀰漫著無望窮人的惡臭,覆蓋了整個印度,甚至滲透到朦朧的天空裡,我從沒體驗過如此境界。我用手帕蒙住我的臉,前往喜馬拉雅山區——達賴喇嘛的流亡居所。我早已旅行過許多地方,可是,我在印度經歷的一連串飯店、計程車與火車,強迫我面對某種我只在書本上看過的絕望:街頭的痲瘋病患、流浪漢的手臂、殘障者、貧苦的人們……
經過將近一星期的旅程,我抵達喜馬拉雅山腳、鄰近印度與巴基斯坦邊界的達拉敦。我立刻動工,雇用了一家製作公司,準備迎接瑞奇到來。在有限的空檔裡,我讀了達賴喇嘛的書《通往自由之路》(The Way to Freedom),並和達拉敦的敏卓林寺的喇嘛交朋友。他們教我怎樣把人骨雕刻成在西藏節慶中使用的號角,並教我一些冥想技巧。瑞奇和他的人已經遲到了幾天,但我活在當下,學習如何享受寺院生活。
電話終於響了,而我只能在電波干擾下辨識出米雷耶.布拉沃美麗的波多黎各口音。「我們不去了!」為了讓我聽清楚,她大聲喊:「我們沒申請到飛到那裡的領空權。」
由於阿富汗處於戰爭狀態,阿富汗官方不允許瑞奇的私人飛機從阿富汗飛到印度。他和所有團隊成員必須折返回巴黎。
我才剛花了幾天時間學習與塵世的利害關係切割,卻因這消息感到心情低落。我擔心達賴喇嘛會因為瑞奇沒來而拒拍公益廣告。然而,我隨即意識到那只是偶發事件,達賴喇嘛是能理解這種事的人。一如我期待的,法王依然熱情地繼續參與拍攝工作。我們只要在回美國後,補拍瑞奇的畫面就行了。洛地嘉日是達賴喇嘛最親近的顧問,聽到瑞奇沒申請到領空權時並不驚訝。「我們一直都拿不到飛往西藏的飛行權。」他笑呵呵地說:「而且也沒辦法飛到其他和中國結盟的國家。」他的聲音與他溫暖的棕色眼睛都毫無苦澀的意味。
他以同樣輕快的語調說:「這件事意味著,或許我們今天的會面是很吉利的事,柯恩先生。」
我們在某個山腳下停車,一群西藏小朋友早已在那裡排隊等著看外國人。我希望他們不會因為只看到我、沒看到瑞奇而感到失望,然而,當我走出車子時,他們全都露出了微笑。
其中一位僧侶向這些孩子打了個暗號,於是他們開始開心地大聲唱出瑞奇.馬汀的名曲《生命之杯》(La Copa de la Vida):「La, la, la...allez! allez! allez!」顯然他們早已練習過了。多特別的一刻!他們甜美的純真,融化了不斷敲擊我腦袋的憂慮:爸爸半夜從家裡打電話給我、哥哥身在戰區、瑞奇.馬汀在巴黎緊張兮兮、少了我的陪伴的派瑞在加州繼續生活。此刻,我感覺自己振作起來了。這些可愛的孩子歌唱、歡呼、跟我握手——不管我是不是搖滾明星,他們真的很高興看到我。
然後,跟那位本尊見面的時刻到了。
達賴喇嘛的私人秘書丹增格西和我走在懸崖邊的小徑上,四周繚繞的山嶺覆蓋著白雪。這是個晴朗的午後,我體驗到的一切——從吹拂我臉龐的風,到地景的色彩——都帶有古老的感覺。風的樂章八方向我們吹送它們的節奏。通過幾個檢查站之後,我可以望見一間小木造佛寺聳立於前方,在天空的襯托下,它彷彿是坐落在懸崖上的小宮殿。另一位僧侶走過來,鞠躬,臉龐閃過一絲微笑,說:「法王就要來了(eminently)。」我猜想他可能是要說「即將」(imminently),不過這兩種說法似乎都適用於此刻。
我站在那裡,突然緊張了起來,雙臂在胸前交叉成祈禱的姿勢。穿西裝、打領帶的我開始微微流汗,舉手摸摸格西別在我領子上、看似徽章的轉經筒。這徽章有如一張貴賓證,確保我能在這座寺院裡通行無阻。
沒多久,出現了一個年紀較大的人,他和其他人一樣穿著簡單的深紅色僧侶袍。從他那獨一無二的笑容與方形眼鏡,我輕易就認出那是丹增嘉措,十四世達賴喇嘛。兩位僧侶站在法王兩側為他撐傘、遮住陽光,六名僧侶和顧問隨侍在後。
「你就是解放奴隸那個人?」他依然溫和地握著我的手。
「尊貴的法王,」我說:「我是把兒童從A點移到B點的人。」我這輩子從未如此謙卑過。
他已看過簡報,知道一些我在蘇丹免除債務運動中從事的工作。他也知道禧年,還告訴我藏傳佛教的喇嘛們對禧年有自己的看法。
「是什麼鼓舞你去解放奴隸?」他突然這樣問我,雙眼依然炯炯有神。我思索了一下他的問題,盡可能以最簡單的方式回答。
「尊貴的法王,我是信徒。」
「喔,是的,你有個希伯來名字。」他說。他仍舊握著我的右手,而且看出我有點不知所措。他調皮地拉拉我的手,笑出聲來,拿我的身高開玩笑,然而他還是一直握著我的手。眼前這個人受盡了苦難,卻沒有露出任何受苦的徵象。他散發著誠懇、謙遜與愉悅的氣息。
我們轉而討論以色列在喪失土地、語言與國家遺產將近兩千年之久,為何仍能維持國家認同並重新建國——這是聖經預言的事件之一。
「那段時期有許多有智慧的人,尊貴的法王,他們認為以色列將再度成為一個國家。」達賴喇嘛挑高了眉毛。眼前這個人失落了他的國家,卻仍然透過他足以鼓舞各種文化的人的教導,使自己的國家繼續存活下來。
我說:「神預言了以色列人將被流放之後,消息傳到所有人耳朵,所以以色列被毀滅的詛咒,最終變成一種祝福。世界大戰以及對猶太人的大屠殺改變了人們的觀點。」
一開始我以為我可能說過頭了,因為達賴喇嘛先回了我一長串「嗯……」,隨後才解釋他對「超脫」的觀點——他告誡我,「這和無分別心不一樣」。他繼續直視著我,眼神似乎毫無閃爍,而且依然冷靜地握著我的手。他提議:「我希望你也能幫助中國的兒童。」我結結巴巴地回應,很驚訝地發現,中國那樣對待他,他第一個關切的卻是中國兒童。
然而,這正是此人不可思議之處。他的言行完全令人無法預測。
接下來那幾分鐘,我努力回答他與他的喇嘛提出的聖經中的歷史問題,尤其是對「一個被佔領的國家如何重建」的看法。我認為他跟我談這些事時的感覺是自在的,因為他看得出來我唯一的目標只是想和他分享havruso這個詞。
「尊貴的法王,」我說:「我想跟你說havruso在希伯來文裡的意思。這個詞源於希伯文的ahavab,意思是『愛』,但並不帶有羅曼蒂克的含意。」
他露出微笑,暗示我該繼續說下去。
「havruso意指『愛人』,不過,這也不是傳統上的含意。它通常用來指稱『與其他學生一起追尋智慧、最後變成真知者的人』。這是另一種『給予他人愛』的方式。」
達賴喇嘛暫停對話,思索這一切,然後開口發出havruso這個字的音。「havruso帶給我們復國的希望。」我說:「因此,我希望你的國家有天能夠重生,尊貴的法王,同時也要感謝你作為全球的havruso,教導了那麼多宏觀遠矚的人。」
我認為他一定很忙,所以心裡一直在等他主動要求離開,但他繼續留下來陪我。他的舉止帶有一種具感染性的帝王莊嚴,而我發現在談話的過程中,我越來越能找回自己的自信。
我們的話題終於進入奴隸制,以及尋找、支持人口販運受害者的工作。我對他說,亞伯拉罕、以薩克與雅各的上帝是聖經記載的第一批奴隸解放者,因為祂帶領以色列人脫離埃及的枷鎖。
法王輕輕鬆開握著我的手,告訴我他已預見到我們的行動將帶來什麼結果。拍攝公益廣告的時間到了,法王以另一個親切的微笑以及些許的誇耀向我表示他該離開了。用完午餐後,我們還會有時間道別的。達賴喇嘛關心我可能餓了或累了,特別交代丹增格西要好好照顧我。
這次謁見的機會原本是為瑞奇.馬汀預訂的,不過,達賴喇嘛讓我感覺我是他最重要的客人。我注意到他對每個人——從廚師到上層喇嘛——都抱持同樣的愛與尊重。我看得出來他舞動的雙眼閃著亮光,而且因為參與我們的工作而開心。
與丹增仁波切、喇嘛們一起用完美味的午餐後,我們錄了一段達賴喇嘛提醒兒童注意人口販運的簡短演說。過了七個鐘頭,我們拍完第二段影片後,法王走過來向我說再見。製作團隊的成員們俯身在法王腳下,法王停下腳步,一個個祝福他們。臨行前,法王再度過來親切地和我握手,露出神聖的笑容,並且再給我一條白色絲巾。當他緩緩走向他那位於丘陵上的寺廟時,他轉身,眉開眼笑,吶喊:「解放奴隸!」
她們每一位都打扮艷麗。
然而,我徹底傾倒在娜奧米的石榴裙下。她是個性感的哥倫比亞美女——五官輪廓分明,充滿了自信。「你想坐哪裡?」她問。
我用西班牙語回答她,她似乎被逗得很開心,當我開始跟她調情、講笑話時,她的笑容變得更興味十足。她引領我走到女侍櫃臺附近的獨立座位區。「我是這裡的經理。」她說:「但瘋狂的是,我今晚也當招待。」她再度微笑,熱情地注視我的眼睛。我完全被這位青春女子擄獲了,她是我見過最美的女人。
「把你自己綁在桅杆上,亞倫。」我內在的聲音提醒我。
這一夜,我一直坐在娜奧米身邊,看她工作,利用她的每個空檔和她聊天。她跟我說她今年二十四歲。
「你知道嗎,我阿姨也叫娜奧米。」當我這樣告訴她時,我感覺到自己呼出的酒精味。
「真的嗎?」她冷淡地說,隨即撥弄髮絲,給我一個挑逗的神情。「所以,你對我的感覺,就像你對你阿姨一樣?」
「是啊!」我應該這樣回答,但我無法這樣對她說。我只是緊張地大笑,彷彿我做錯了什麼事被抓包一樣。
「好吧!」她說:「我猜你希望找個比我年輕的。」這當然不是真的,可是我提醒自己正在工作,讓她繼續講下去。「所以,我會叫一些美女來陪你。」她眨眨眼。
接下來那幾個小時,娜奧米帶了許多年輕女子來見我,她們的年齡都介於十七歲到十九歲之間,而且都穿比基尼,外頭裹著鮮豔的緊身衣,每一位都比上一位還漂亮。她們大多來自麥德林。我遵守禮節,微笑,幫每位女孩付飲料錢,給她們小費。不過,我成功地讓娜奧米明白我對這些女孩都沒興趣。
街道上的細碎燈光照進來,鋪在這些女孩回房的通道。這時,娜奧米走過來,滑上我身邊的雅座。「我只帶最棒的女孩來見你,而你還沒有找到你想帶回家的人?」她挑逗地說。
「我寧可和你回家。」我終於說。希望我的誠實待會兒能讓她提供我可靠的消息。我確定這女人可以引導我找到我想找的人。
「所以,你為什麼不這樣做呢?」她半笑半氣地回答我,然後突然站起來,大步走向出口。我沒拿到帳單,不過,我在走出去時給了另一個經理和保鏢小費。我們跳進一輛計程車。娜奧米張開雙手貼在我身上,我們接吻了一下,光是這樣,已火熱得足以讓我知道:今晚要把我自己綁在桅杆上,將會非常、非常困難。
和娜奧米手牽手走在飯店的長廊上時,我很擔心會遇到蜜雪兒。如果她撞見娜奧米和我在這裡,一定會不高興的。我已經對她說過我打算帶女孩回來我房間——她說她可以了解我的動機——但我不確定她是否完全信任我。
*
我了解,如何使人卸下防衛心,與所有受害者、媽媽桑及人口販子輕鬆相處,將會是我成功的關鍵。但蜜雪兒無法體會。
有天晚上,在賭場,蜜雪兒走到我身邊,望著我的某個消息來源坐在我腿上玩我的頭髮、撫摸我的胸膛,另一個消息來源跟我靠得很近,和我一起大笑、公然調情。蜜雪兒看起來並不開心;事實上,我感覺她徹底厭惡這種事。她低聲嘀咕了幾句,露出憤怒的表情,隨即大步走出賭場。這場戲本可就此打住,但蜜雪兒太急了,因而踩到地毯邊緣,迎面跌倒在地上。我趕緊跑過去扶她起來,可是她拒絕接受我的幫忙。那是我們雙方第一次對於「界線」的意見產生分歧。
「你太超過界線了。」她說。
「界線的範圍,端視我是否有能力抗拒一般男人覺得無法抗拒的誘惑。」我記得我這樣告訴她。「你已經了解我並不像大多數男人那樣。如果你想看到成果,你必須讓我決定自己的界線。」
那天晚上,蜜雪兒沮喪地嘆氣,離開我身邊。我了解她想保護這些女人,她真誠地渴望讓她們每個人都不再受虐。然而,我知道如何在性工作者的世界裡行事,你永遠無法在這種世界裡畫出清楚的界線。自此之後,我們都同意讓我自己掌握「界線」。
這趟旅程,我們協議各別住在不同的樓層。如果有人問起,我會說蜜雪兒是我表姊或工作伙伴,我們一起做兒童慈善工作,來這裡是為了公事。
*
一進我房間,娜奧米就迅速脫掉胸罩和內褲,而我則努力解釋為何無法和她親熱。「你真的很迷人。」我告訴她:「我真的喜歡你,可是我在故鄉有女朋友。」我說出這些話時,我立刻了解這聽起來有多荒謬,不僅因為這種謊言是陳腔濫調,而且我最後一任女朋友才剛離開我、投入別人的懷抱,她說她沒辦法不去想我從事的工作。
實情是:我單身,而且深深受這女人吸引。
她噘起雙唇,冷冷地凝視我的眼睛。「你女朋友不在這裡。」她實事求是地說,同時開始脫我的襯衫。
我努力不去看她那無瑕的肌膚、棕色的捲髮、及線條完美的手臂,專心思考如何在自己不洩底的前提下讓她信任我。我讓她脫掉我的T恤和拳擊短褲。
「娜奧米,」我再度嘗試:「我真的很喜歡你,可是我有點迷惑,我不知道該怎麼做,所以,請讓我們單純地抱在一起睡覺。」
她再度露出被逗樂了的表情。「好,亞倫。不過,明天你要和我狂歡。」
「就這麼說定了。」
我們爬到床上,身體交纏在一起。她開始跟我說她的生命故事,怎樣在十四歲時從哥倫比亞被販運到這裡,清償她的債務,然後升上經理的位置。「因為我有一百萬個情人,」她凝視著我:「雖然他們沒一個好東西。」
她再度湊過來吻我,我立刻感覺到自己亢奮起來。娜奧米扭動身子靠近我,我緊緊抱住她的肩膀,把手指放到她唇上,叫她冷靜下來。然後,我強迫她的身體保持不動。她不斷努力反抗我,但是,我只是緊緊擁抱她,假裝睡著了。很快地,她也沉沉睡去了。
我試著單純地享受與這細膩、有魅力的女人親密共處,然而,我的身體在和我的大腦奮戰——為了不去撫摸這女子而備受折磨,為了需要我們幫助的兒童,也為了蜜雪兒可能會突然跑進來撞見這景象、誤解一切。
感謝上帝,我想我終於能打個盹了。
我開始不自在了起來,腦袋輕飄飄的,四周的顏色過於顯目。我注意到娜奧米和她的幾個「朋友」在吸古柯鹼,於是懷疑她是否給我吃了什麼東西。我停止喝飲料,一逮住機會就把她推到一旁。
「你是不是在我的飲料裡摻了什麼東西?」我看著她呆滯的眼神說。她拒絕看我,這下子換我生氣了。
我不能讓自己在這裡失去控制。周圍有太多危險的人。
「亞—倫,亞—倫……我只是希望你能跟我在一起,快樂起來。」她以西班牙語難過地說:「我真的很抱歉。」她湊過來吻我。
我努力保持冷靜,不讓自己的頭腦飄進太空。我曾經歷過這種狀態。我早已學會如何在吸毒時保持頭腦冷靜,而這正是我此刻該做的事。
毒品已經將娜奧米送往另一個世界,她開始狂野地抓著我。「回到屋子裡,跟我跳舞、讓我們狂歡!」她說。我決定做些讓步。我雖然對她在我飲料裡摻東西感到生氣,但我不能錯過參觀拉烏爾.古鐵雷斯的房子的機會。
「娜奧米,你知道我是來這裡幫助兒童的。」我開始說明我的目的了。
「是啊,而且我愛這樣的你。」
「好。對你來說,兒童是幾歲?」我問。
「我不知道……小於十四歲?」她疑惑地看著我。
「我也不知道。可是,看到在歌舞女郎工作的年輕女孩,真的讓我很難過。」我說:「我不認為她們想留在那裡。」
「當然不囉!」她說:「她們被迫工作,就像我以前一樣。」
聽到她說得這麼直接,我開始生氣了。「那麼,為什麼你不幫助她們?」
她的表情告訴我,我越界了。「我很抱歉。」我說:「這些毒品讓我變得怪怪的。我們離開這裡吧。」
「好。」她說:「我們去參加餘興派對。」
我們搭上這晚的第四趟計程車,停在另一間百萬豪宅前。我認出屋外的某些車子是來自前一個派對的人。客廳裡有個水幕和一個很大的熱帶魚缸。時鐘指著凌晨四點,這場派對才剛開始。一群人排在咖啡桌前吸古柯鹼,其他人則拿著雞尾酒杯隨拉丁流行歌曲起舞。
我認出一個穿著光鮮、年紀較大的男人是歌舞女郎的老闆之一。他走向我,伸出手來,我認為這姿勢比較像是挑釁而非溫暖的歡迎,不過,我決定跟他握手,試著讓他放鬆。
他自我介紹說他是拉烏爾.古鐵雷斯。
娜奧米告訴他我是音樂家、她的朋友。我提起慈善工作,以防有人交叉比對我的背景。古鐵雷斯陪我們走到吧台,叫我們想喝什麼就點什麼,然後就消失了。幾分鐘後,娜奧米帶我走到樓上的一個包廂,裡面有一張沙發和幾張椅子。當她開始嘗試吻我,拉烏爾和幾個朋友帶著吉他走進來。
「這個給你,我的音樂家朋友。」他對我眨了一下眼睛,把吉他遞給我。這也是個挑釁,不是友善的舉動。我點頭接受了。
「你今晚和娜奧米參加過派對?」他問。他的雙唇舞出一抹微笑。
「是啊,我們參加過派對。」我努力回給他一個微笑,讓他知道我並不緊張。再一次,我感謝搖滾樂。我拿起吉他。
我就是知道要彈什麼。我開始漫不經心地彈幾個小節,進入我幾年前曾為派瑞演奏過的旋律,席維歐.羅德里葛茲的Oleo de Mujer con Sombero,一首悲傷而浪漫的拉丁美洲左派名曲。我注入自己的情感,想起我失落的愛情以及我的毒癮,將我的心與音樂連結在一起。
我深深沈浸於這首歌裡,幾乎忘了我正在為一群毒梟與他們的女人演奏。因此,當我彈完時,我突然因為聽到他們熱烈的掌聲與歡呼聲而嚇了一跳。
古鐵雷斯以眼神和我交流,點頭表示讚許。我笑出聲來,此刻徹底放鬆了。
古鐵雷斯和我聊了一些美國人在玻利維亞採錫礦、在亞瑪遜森林採石油與林木的事情。我在秘魯和阿根廷的經歷,讓我得以與他進行流暢的對話。「如果你進來這裡強暴一群女人,你就很難讓他們按照你的人權建議來做事。」當我這樣說,我甚至沒想到古鐵雷斯的事業是在奴役哥倫比亞一整個世代的女性。他只抓取我的主要隱喻,點頭同意我的說法。
我被他們接受了。
接下來幾個小時,娜奧米跟一些女性友人玩、和古鐵雷斯談生意,我則和他手下的幾個人聊天。我挖掘出許多他們的運作方式,而且發現那其實非常有系統。這些女孩大多是來自麥德林或恰勒,她們在網站上回答徵模特兒廣告的問題,因而被招募進來。「太糟了!」她們收到的通知說:「你的條件不太符合當模特兒的標準,不過,我們可以給你其他賺大錢的機會……。」被招募進來的女孩大多超過十六歲,可以隨意自由進出。可是,有些孩童卻陷於黑暗中。他們大多是還在上初中的女孩與男孩,被安置在秘密的處所,以高價售出他們的服務。沒人想談這些兒童。我步步為營,小心不洩漏我的身份。
我和娜奧米離開古鐵雷斯的豪宅,強烈感覺到這個古柯鹼黑道的勢力相當龐大,而且毒品與人口販運關係密切。同時,我深刻體會到,我們每個人都與這問題及其解決之道息息相關。
娜奧米和我在早餐時分回到我的飯店房間。喝酒和跳舞強化了她的慾望,她渴望親熱。她噘起嘴唇,忘情地撫摸自己的頭髮,壓在我身上。我必須很用力才能掙脫她,最後幾乎跟她扭打了起來。如此美麗的女人,總是不習慣被拒絕。我繼續說我前一晚未說完的故事,可是,因為參加派對和喝酒,我尚未築起防衛心。我們接吻,在床上扭成一團。娜奧米身上的毒品作用已經消退,突如其來的精力使她變得沮喪。我們之間的性張力仍在高漲。我離開她身邊,因為蜜雪兒隨時都會來敲門。
「你到底怎麼了?」娜奧米說,「你跟我說你有女朋友,可是你又帶我回來這裡,然後你不想要我?或許你並不是真正的男人。」她忘了自己的目的,笨拙地攻擊我。
我是多麼飢渴地想要她,卻努力讓自己冷靜。慾火在我和這女人之間燃燒。「聽好,娜奧米,我才剛認識你。我家出了點問題,我只是需要多點時間來整理自己的感覺。」實情是:我珍惜我倆的親密關係,雖然我必須用謊言騙她來這裡。
我抓住她,抱起她,把她帶到床上,跟前晚一樣,我們單純地擁抱睡覺。這一次,她完全沒掙扎就睡著了。
輕微的敲門聲吵醒了我,我開門,看到蜜雪兒站在門外。已經下午一點多了。她從門口環視屋內,觀察這場景:穿著內褲的我、蜷曲在床上睡覺的娜奧米。
「我在樓下和你會合。」她簡略地說。






.png)